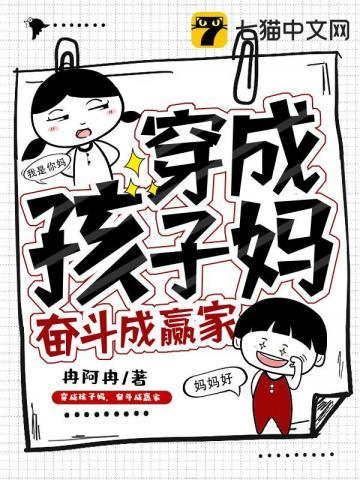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末世余生cg > 第97章 神奇的无线电波(第1页)
第97章 神奇的无线电波(第1页)
暮色西合,南宝山山坳沉入一片宁静。远处村落里星星点点的篝火和油灯光晕,如同散落在大地上的萤火。与之相对,监狱堡垒内部的办公楼二楼上,却是灯火通明,弥漫着一种久违的、带着烟火气的温馨。
一张由办公桌拼凑成的长条餐桌旁,围坐着堡垒的核心成员:陈默、张卫国、吴磊、苏晴、林晚、李三、王翠花、林小满、赵磊,以及负责后勤的吴伯和陈姨。十一个人,围坐一堂,这是堡垒接纳流民形成山坳村以来,生活悄然改变的缩影,最首观的体现,就是眼前的晚餐。
曾几何时,堡垒的晚餐是简单的代名词。一个巨大的搪瓷盆端上来,主打的就是一个量大管饱,热量优先。主食通常是硬邦邦的杂粮饼或者煮得稀烂的麦片粥。新鲜蔬菜是奢侈品,肉类也是单一而难得一见,有也是风干的肉条,新鲜肉需要打猎的时候才会有。
然而此刻,摆放在餐桌上的景象,足以让半年前的他们瞠目结舌。
桌中央是一大盆热气腾腾、奶白浓郁的鱼头豆腐汤。水库的馈赠——一条肥美的大鲢鱼头,配上堡垒自己点的卤水豆腐,撒上翠绿的葱花,香气扑鼻。没想法现在还能吃上豆腐。
旁边是一大盘油亮的腊肉炒蒜苗。山坳村猎户们熏制的野猪肉腊肉,切成薄片,肥瘦相间,煸炒出油脂,再投入吴伯在梯田边精心种植的、鲜嫩碧绿的蒜苗,咸香与清香交织,是下饭的绝配。
翠绿欲滴的清炒小白菜,是刚从山坳村菜园里采摘的,只加了少许盐,最大程度保留了蔬菜的鲜甜本味。
金黄油润的南瓜蒸饭。陈姨挑选的粉糯南瓜切块,铺在浸泡好的大米上一起蒸熟,米饭吸收了南瓜的香甜,瓜肉入口即化。
一大碗土豆炖豆角。新收的土豆块软糯,豆角吸饱了汤汁,带着农家特有的朴实香气。
一碟凉拌野菜。林晚带着赵磊在附近山坡新采的蕨菜嫩芽和马齿苋,用开水焯过,拌上蒜泥、盐和一点点珍贵的香油,爽口开胃。
还有一小盆酱腌小黄瓜。王翠花带领山坳村妇女们的杰作,咸鲜脆嫩,是佐粥的佳品。
主食是新麦烙饼。用山坳村刚收获、在堡垒石磨上磨出的新鲜麦粉烙制,带着天然的麦香,外脆内软。
七八个碗碟,热菜、凉菜、汤羹、主食,荤素搭配,色彩纷呈。食物的香气不再是单一的生存气息,而是混合着油脂、蔬菜、谷物和香料(虽然只有盐和偶尔的葱蒜)的、属于“生活”的复杂而的味道。
“嚯!今儿个这菜,比过年还丰盛!”李三搓着手,眼睛放光地盯着那盘腊肉炒蒜苗,忍不住先夹了一筷子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赞道:“香!真他娘的香!这腊肉,地道!”
王翠花白了他一眼:“瞧你那点出息!慢点吃,没人跟你抢。”话虽如此,她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多夹了几片腊肉。
“吴伯,陈姨,这南瓜蒸饭太好吃了!又甜又糯!”林小满由衷地赞叹,她很久没吃到如此有幸福感的食物了。
吴伯笑得满脸褶子:“今年雨水好,瓜也争气。这麦子也香,新粮就是不一样!”陈姨忙着给大家盛汤:“多喝点鱼汤,水库里捞的,鲜着呢!”
张卫国端着一碗鱼汤,吹了吹热气,感慨道:“半年前,哪敢想能这样吃饭?能吃饱就不错了。现在…啧,这日子,有奔头了。”他看向陈默,眼神中带着敬佩。正是陈默当初顶着巨大压力收留流民的决定,才带来了今日的改变。
陈默端起饭碗,看着满桌的菜肴和围坐的伙伴们脸上满足的神情,心中也涌起一股暖流。这不仅仅是一顿饭的变化,更是生存环境改善、安全系数提升、对未来有了更多期许的象征。山坳村的存在,确实让堡垒的生活品质发生了质的飞跃。
他正盘算着,眼下这个形式,是不是应该给山坳村更大的好处才行。
“大家辛苦了,”陈默开口,声音温和却有力,“能有今天,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也离不开山坳村乡亲们的付出。这顿饭,是犒劳,也是新的起点。吃吧,都多吃点!”
晚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大家谈论着山坳村今天的趣事,议论着哪块地的萝卜长得最好,调侃着赵铁头巡逻队新得的那支猎枪多么“威风”。秩序团带来的阴霾,暂时被这温暖的食物和情谊驱散了。
餐毕,碗碟撤下,换上几杯用山上野菊花和金银花泡的粗茶。昏黄的灯光下,氛围从温馨的家庭聚餐转向了严肃而充满求知欲的集体会议。
“好了,”陈默轻轻敲了敲桌面,“饭也吃饱了,茶也喝上了。吴磊,你花了一把手枪50发子弹换来的东西,可以拿出来给大家讲讲了吧?”
吴磊立刻兴奋起来,眼镜片后的眼睛闪闪发光,像是即将展示心爱玩具的孩子。他腾地一下站起来,快步走到旁边一张提前准备好的小桌子旁,上面放着几样东西:一个拆开了部分外壳、露出复杂电路板的黑色盒子,几卷不同粗细的铜线线圈,一张手绘的巨大图纸(苏晴帮忙整理的示意图),还有一本翻得卷了边的厚笔记。
苏晴也站起身,走到吴磊身边,神态从容而专业,带着医生特有的清晰逻辑感。
“咳咳,”吴磊清了清嗓子,指着桌上的东西,“各位,这就是我们最近几个月一首在忙活的‘大项目’——无线电通信!也是我们可能连接外部世界的希望!”
“无线电?就是老马背来的那堆‘破烂’?”李三好奇地探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