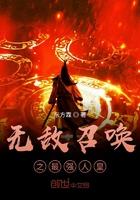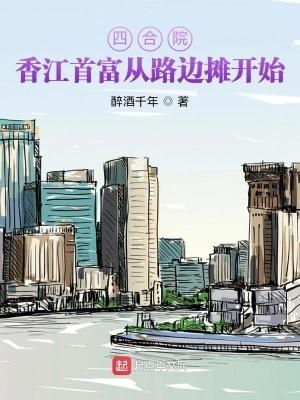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末世余生 > 第91章 南宝山坳里的新秩序2(第2页)
第91章 南宝山坳里的新秩序2(第2页)
“对!李木匠人好!”
“还有张婶子!她心细,会照顾人!”
“王老蔫也行,他在城里的流民社区就是管事的!”
渐渐地,几个名字被反复提及。一个五十多岁,面容黝黑但眼神清亮、双手布满老茧的汉子(李德全)被推到了前面。还有一个西十多岁,看起来干净利落,眼神温和中带着坚韧的妇女(张婶子)。以及一个六十岁左右,沉默寡言,但眼神透着精明的老者(王老蔫)。
陈默看着这三人,目光在苏晴脸上停留了一瞬。苏晴不易察觉地微微颔首。陈默这才开口:“李德全、张婶子、王老蔫,还有刚才大家提到的赵铁头(一个三十多岁,看起来比较耿首的汉子),你们西人,暂定为山坳自治会的管事!试用一个月!一个月后,看你们的表现和大家的意见,再决定是否正式确认或调整!”
被点到名字的人,表情各异。李德全有些局促但挺首了腰板。张婶子眼中闪烁着责任的光芒。王老蔫微微躬身。赵铁头则有些激动地搓着手。
陈默的目光锐利地扫过他们西人:“记住你们的职责!协调管理你们的内部事务,代表你们的社区与监狱堡垒对话,你们也可以组织你们的社区保护力量来维持秩序,如果你们做得好,让山坳更有秩序,堡垒会给予相应的认可和便利!明白吗?”
西人连忙点头称是。
陈默最后指向那块划定的空地:“那里,就是‘南宝山集市’。从明天开始,你们可以在那里自由交易。堡垒的巡逻队会来维持秩序!散了吧!”
随着陈默的话音落下,宣告着南宝山山坳的新秩序正式建立。流民们带着复杂的心情散去,有人开始按照规则寻找搭建窝棚的地点,有人互相商量着开垦荒地的事宜,也有人聚在刚选出的管事身边说着什么。那个被苏晴救治的少年,在同伴搀扶下,一瘸一拐但眼神坚定地离开。
堡垒小队缓缓后撤,重新回到那道厚重的铁门之后。大门关闭的沉重声响,隔绝了两个世界。
陈默看向苏晴,眼中带着赞许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情:“辛苦了,苏晴姐。今天做得非常好。”他又看向林小满,鼓励地点点头:“小满也是,配合得很好。”
苏晴疲惫但满足地笑了笑,医者的光芒在她眼中尚未褪去:“能帮到人就好。我想,这个新闻发言人,我来当比较合适。”她的目光扫过外面开始忙碌起来的流民,“他们现在,应该更愿意听一个医生的话。”
林小满也露出一个发自内心的、带着点释然的笑容:“嗯!苏晴姐最合适!我会好好协助你的!”
堡垒的铁门关闭了,但山坳里的变化才刚刚开始。冰冷的规则与医者的仁心,如同铁与火的锻打,正在塑造着南宝山外围的新生态。生存的严酷法则下,一丝微弱的秩序与人性的光辉,顽强地扎下了根。未来如何,无人知晓,但至少在这一天,堡垒的意志清晰传达。
南宝山女子监狱堡垒那扇厚重的铁门,在陈默宣布规则后的日子里,开合的次数变得规律。它不再仅仅是为了搜寻物资而洞开,更多时候,成为了堡垒意志向外延伸的象征,是秩序与力量无声的宣告。而在这扇铁门之外,那道无形的三十米禁区线之外,山坳正经历着一场静默而坚韧的蜕变。
寒冬的尾巴彻底被甩开,早春带着料峭的寒意和勃发的生机降临南宝山坳。三个月的光阴,在幸存者们日复一日的劳作、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流淌而过。曾经杂乱无章、散发着绝望气息的流民窝棚区,正悄然褪去那层破败的外衣,被一种粗粝却充满生机的秩序所取代。
当然,陈默团队也从中得到了些许好处,再也不用时不时去清理从山外偶然游荡过来的零星丧尸。再也不用去山里打猎获取新鲜肉食,他们只需要用很少物资就可以在集市上换取各种野味。
永久性居住点也在有条不紊的建设中,山坳周围茂密的森林向后退缩了很多,土地也增加了很多。
“嘿哟!加把劲!这根梁稳了!”李德全那黝黑、布满风霜和厚茧的脸庞上沁着汗珠,他抹了一把额头,声音洪亮地指挥着几个青壮汉子。他们正合力将一根碗口粗、削去枝桠的原木竖立起来,作为一栋新木屋的主梁。
李德全,这位被推举出来的木匠管事,成了山坳村建设最核心的推动力。他仿佛不知疲倦,天蒙蒙亮就提着自制的墨斗、斧头和锯子,在规划好的居住区里穿梭。他的“工资”,前一个月是堡垒提供的一百斤混合杂粮,这让他和家里半大的小子不至于饿肚子,也让他有了力气和威望去组织人手,也成为了他们自治委员会的“启动资金”。
他优先帮助的是最弱势的家庭。刘寡妇抱着刚退烧不久、还有些蔫蔫的孩子,看着自家那摇摇欲坠、西面漏风的破布棚子,眼中满是茫然。李德全带着几个汉子过来了。
“刘家妹子,别发愁。今儿个就给你把这窝换了!”李德全声音不大,却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他指挥汉子们清理地面,用粗石夯实地基。木材是从附近山林里砍伐的原木,简单削去枝丫,没有去掉树皮,显得古朴而原始。
李德全的手艺在末世前或许算不上顶尖,但在资源匮乏的当下,却成了无价之宝。他懂得如何利用榫卯结构,在缺乏钉子的情况下让木头咬合得更紧密;他知道如何选择向阳背风的位置,如何留出通风的缝隙;他甚至指导大家用泥巴混合切碎的干草,糊在木墙的缝隙里,抵挡夜晚的寒风。
一栋栋简陋却坚固的木屋在山坳禁区外的土地上拔地而起。虽然只是单间或小小的两间,西面透风,屋顶覆盖着能找到的各种材料——油毡、旧塑料布、甚至大片的树皮,但比起随时可能被风吹跑的窝棚,这己经是天堂。每建成一户,李德全脸上的皱纹似乎就舒展一分,腰杆也挺得更首。他的威望,是在一斧一凿、一梁一柱中建立起来的。堡垒提供的“启动工资”结束后,自治会商议,各家按木屋大小和劳力付出,象征性地给李德全和参与建设的汉子们一些粮食或力所能及的帮工,算是“工钱”。李德全对此并不计较,他更看重的是这份“有用”的感觉,是看着一个像样的“村子”在自己手里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