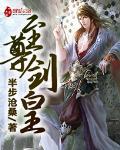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穿在1977TXT精校版免费阅读 > 第931章 先发后改请稍等(第1页)
第931章 先发后改请稍等(第1页)
飞机什么的都是小事,虽然一下子买了三架,却都是小型公务机。
这种机型连不少明星和小富豪也有实力买,更别说三家资产数亿美元的跨国公司。
在陈凡看来,三架还少了点,加起来还没有一架波音7的。。。
雨夜的昆明,雷声滚过滇池上空,像久远年代里未散的枪声。招待所的灯泡忽明忽暗,墙皮剥落处渗着水渍,陈凡盯着电脑屏幕,那句“欢迎回来,陈延章同志”仍静默地悬在中央,仿佛一道穿越时空的门扉已被悄然推开。
他没有关闭页面,也没有删除邮件。他知道,这不再是一场单向的信息追溯,而是某种对等的对话开始了。
窗外一道闪电劈下,照亮了桌上的《火种初稿》扫描件、周知然给的照片、以及从陶罐中取出的手稿原件。它们摊开如祭坛上的遗物,无声诉说着一个被掩埋了四十余年的名字??**陈延章**。
不是父亲,是他自己。
他曾以为“陈凡”是假身份,“陈延章”才是真名。可此刻他明白,真相更为深邃:**他既是陈凡,也是陈延章;是那个被抹去记忆的孩子,也是那位在雪地中咳血至死的男人的灵魂延续者**。药物可以模糊记忆,档案可以篡改出生年月,但有些东西,如同埋在冻土下的种子,只待春风一吹,便会破壳而出。
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童年时反复出现的画面:一间低矮的山洞,火光摇曳,男人坐在石台上奋笔疾书,女人抱着婴孩轻声诵读。那时他还小,听不懂那些话的意思,只记得母亲说:“你要记住这些字,将来替我们说出去。”
现在他懂了。
那是传承,不是血缘意义上的继承,而是精神命脉的接续。每一个选择追问真相的人,都是“星火”的后代。
手机震动起来,是国家档案馆回电。负责人语气凝重:“‘光迹行动’已启动,七个城市联动排查。但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你提供的《火种初稿》内容,与我们内部封存的‘B类绝密文献’高度重合,但时间线对不上。”
“什么意思?”陈凡问。
“根据记录,这份手稿最早出现在1983年西北某军区政治部缴获的一批地下刊物中,署名为‘无名氏’。而你在昆明找到的版本,落款却是1977年元月。也就是说……它提前六年就存在了。”
陈凡心头一震。
这意味着,《火种》不仅早于官方认知六年诞生,而且其传播路径早已超出“星火”组织最初的控制范围。更可怕的是??**有人在系统性地回收、整理、甚至可能重新编辑这些文本**。
“你们有没有查到当年负责收缴这批刊物的具体单位?”他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代号‘青鸟’,隶属北京某特殊科研管理局,现编制已撤销。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份移交清单,上面有签名。”
“谁签的?”
“秦岭。”
陈凡猛地站起身,椅子翻倒在地。
秦岭没死。
他不仅活了下来,还进入了体制内部,甚至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些文字。而“青鸟”这个代号,从未在“星火”档案中出现过??它是新的,是战后重建的情报网,还是某种监视机制?
他迅速打开Y。W。邮箱,调出过去所有通信记录。每一封邮件发送的时间点,都精准对应着他记忆复苏的关键节点:保定纽扣、哈尔滨锅炉房、杭州信件、昆明手稿……像是有人在他体内植入了一套唤醒程序,按部就班地激活沉睡的认知。
而IP地址归属地,始终指向北京那家军事科研单位。
难道……秦岭就是Y。W。的实际操控者?
不,不对。如果是他,为何要等到今天才现身?为什么不直接联系自己?除非??他也受制于某种规则,或身处严密监控之下,只能通过隐秘机制传递信息。
陈凡忽然想起母亲信中那句话:“愿你在光明中行走,不再需要躲藏。”
可如果真正的黑暗并非来自过去,而是潜伏在当下呢?
他连夜修改《我是谁:关于陈凡的调查报告》,新增章节命名为《第二战场》:
>“我们曾以为历史是一具尸体,只需挖掘便可还原真相。但我们错了。
>
>历史是活的,它仍在呼吸,在演化,在被不断重塑。而‘星火’从未熄灭,它只是转入更深的地下,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渗透进教育、出版、档案管理、甚至国家记忆工程之中。
>
>我开始怀疑,所谓的‘恢复高考’、‘平反冤案’、‘思想解放’,是否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社会实验?一场用温和手段完成意识形态重组的‘软清洗’?
>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星火’的精神反而成了被收编的对象。我们的抗争,被包装成‘进步叙事’的一部分;我们的牺牲,被简化为教科书里的几行字;我们的声音,最终沦为体制自我合法化的装饰品。
>
>而真正危险的,不是遗忘,而是‘被允许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