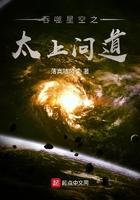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1909年2月1号中日英法俄德美葡等国召开禁毒会议 > 第69章(第2页)
第69章(第2页)
郝思倍脸色剧变,忙跳上前去。我与郑正卿紧随其后。
在许多条木船中,这一条格外破旧,我一脚踩上去,湿冷寒意渗透足尖:这船底,竟已漏入了两寸深的水。
船头挂着一盏发黑的油灯。
那灯罩早破了,裂缝中,透出微弱的光来。
一个面色愁苦的女人,拿着一个破烂的包裹。
岸边一个男人,一把破伞,女人正要随他而去。
那叫小元的男孩,死死拉着她:“你不是说,凑够了钱,就不会卖她吗?”
他带着哭腔:“钱凑齐了!我妹妹呢?”
那女人形容枯槁如死灰:
“她早被人带走了……小元,你不要怪娘。我跟你们的爹,不过半路夫妻。”
这女人,原是小元的后娘——
“他抽大烟死后,留下这么多债,我这几年,太难了。这渔船上一年比一年差,还要照顾你们……”
小元愤怒至极:“我们都是自己讨饭吃,什么时候用你照顾!”
郝思倍上前抱住小元:“孩子……”
小元颤抖着声音,只盯着那女人:“我娘走的早,妹妹从小管你叫娘,懂事起就帮你干活,讨来的饭菜总带你吃!你……竟把她给卖了!”
他的脸上,泪在雨中,一时难辨:“凭什么!”
他挣脱了郝思倍,上前就要动手,一旁的男人欺上前去:“你干什么!”
郑正卿在旁阻拦不及,那男人对小元一番拉扯,这后娘喊道:“别伤了孩子!”
她上前护住小元——
这即将被她抛弃的孩子。
我不由叹息:“我看你也不是绝情的人,你要改嫁,何苦卖他妹妹?”
那后娘不敢与我对视,只羞愧道:
“我也是为他妹妹好,离了这里,还能有一条活路……”
她回头看这一条条木船:“我也是木船上长大的,岸上的男人,哪有几个愿娶船上的女人?留在这,只有一辈子吃苦的份。”
她说的,倒也是事实——这些船上的女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总被陆地上的人们歧视。
终其一生,只能从一条船,嫁到另一条船。
这后娘回身,搂住小元道:“你亲娘怎么去的,你忘了?生了重病动不了,大夫又不愿来,最后人没了,直接扔下河去……”
那小元倔强地抹着眼睛,只看着那静静的河水。
幽深的河,曾吞没他母亲的身体。
惟有千重浪,卷起无字碑。
那后娘道:“你爹去后,多少人劝我改嫁,我都舍不得你们。你和你妹妹哪回生病,我不是夜夜守着?可是……”她哽咽着:
“咱娘三个若这样下去,只有一同饿死。”
这后娘看着那一旁男人:“如今,他愿意带我上岸,娘也是没办法了……”
她的双脚,已站到了岸边。
男人撑的不过一把破伞。
却已足够使她逃离——
那风雨孤舟。
她伸手入雨中,轻抚了一下小元的脸:
“家里还有最后一点米,我都放好了在缸里。你的衣服,一件长的两件短的,娘也为你补好了,都叠了在枕头下……娘走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