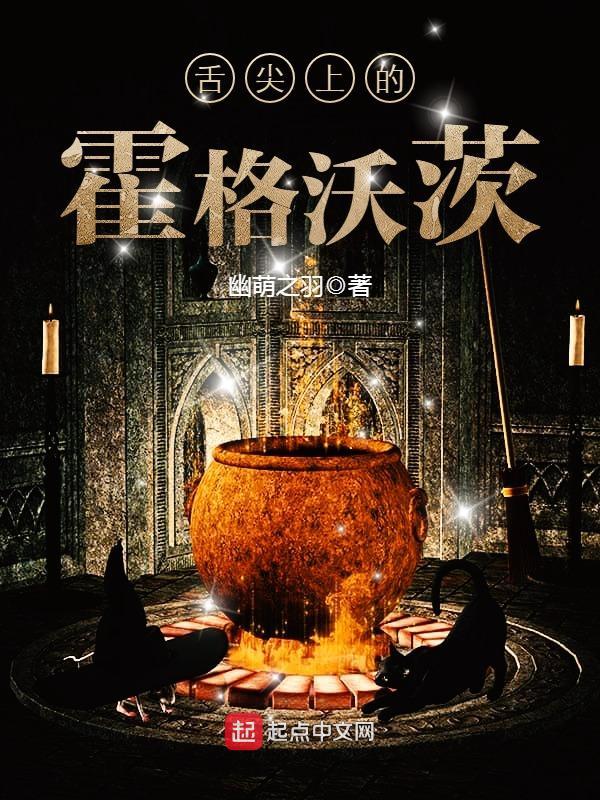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总裁是老婆的 > 第6章 烙印之书臣服的终章(第5页)
第6章 烙印之书臣服的终章(第5页)
“这就受不了了?”
“野兽”的声音带着戏谑,非但没有放缓,反而故意加重了步伐,甚至坏心眼地小跑了几步!
“呀啊——!”剧烈的颠簸让那根东西在李慕辰体内横冲直撞,每一次落点都又深又重,撞得他魂飞魄散,前端不受控制地渗出清液,内壁疯狂地痉挛绞紧。
极致的快感混合着巨大的羞耻感,如同海啸般将他淹没。
他再也顾不得其他,放声哭喊起来,淫词浪语不受控制地倾泻而出:
“老公……操死我了……好深……要坏了……啊啊……我是你的骚货……你的淫娃……呜呜……好舒服……再重点……”
他的哭喊和求饶仿佛是最好的催情剂,“野兽”的呼吸愈发粗重,抱着他的手臂收得更紧,步伐也越来越快,撞击得愈发凶狠。
客厅,走廊,餐厅……他们所过之处,只剩下李慕辰破碎的呻吟和肉体激烈碰撞的淫靡声响。
不知过了多久,就在李慕辰觉得自己快要被活活操死在半空中时,“野兽”猛地一个深顶,将他死死钉在墙上,滚烫的工业精华激烈地喷射进他身体最深处。
李慕辰同时达到了高潮,身体剧烈地抽搐着,发出一声长长的、近乎断气的呜咽,前端喷射出的白浊弄脏了彼此的小腹和家居服。
高潮的余韵中,李慕辰浑身瘫软,像一滩烂泥般挂在“野兽”身上,连呼吸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野兽”抱着他,走到沙发边坐下,却并没有将他放下,而是让他跨坐在自己腿上,那根刚刚释放过的欲望依旧埋在他体内,微微搏动。
他调整了一下姿势,让李慕辰靠在自己怀里,然后,做了一件让李慕辰意想不到的事——他捧起了李慕辰那只穿着白色短袜的脚。
“我的辰辰,连脚都生得这么好看……”
“野兽”的声音带着事后的沙哑和一种近乎痴迷的赞叹。
他低下头,竟然如同品尝美味般,伸出舌头,从袜口处露出的纤细脚踝开始,沿着脚背,一路舔舐到圆润的脚趾。
湿热的触感透过薄薄的棉袜传来,带着一种极致的羞辱和奇异的痒意。
李慕辰脚趾敏感地蜷缩起来,发出细微的抗拒声:“别……脏……”
“脏?”
“野兽”轻笑,非但没有停下,反而舔弄得更加卖力,甚至用牙齿轻轻啃咬他敏感的脚心,“我的东西,怎么会脏?”
他舔了好一会儿,直到那只白袜被口水濡湿,颜色变深,紧贴在脚上,勾勒出清晰的轮廓。然后,他拿过旁边桌上那瓶喝了一半的昂贵红酒。
在李慕辰惊愕的目光中,他拔掉木塞,将殷红的酒液,缓缓地、均匀地倾倒在那只被他舔湿的脚上。
冰凉的液体激得李慕辰一颤。红酒顺着脚踝流淌,浸透了袜子,染红了原本洁白的颜色,滴滴答答地落在地毯上,晕开一片深色的痕迹。
“现在,”
“野兽”放下酒瓶,再次俯下身,眼神幽暗,“让我尝尝……红酒洗过的脚,是什么味道……”
他如同最虔诚的信徒,又如同最贪婪的饕客,开始用唇舌,耐心地、一寸寸地,舔舐清理着那只被红酒浸染的玉足。
从脚踝到趾缝,不放过任何一滴酒液。
湿滑的触感,混合着红酒的醇香和唾液黏腻的感觉,带来一种无法形容的、堕落到极致的官能刺激。
李慕辰仰着头,靠在“野兽”坚实的胸膛上,身体还在微微颤抖,大脑一片空白。
身体的极度疲惫,混合着这诡异而羞耻的侍奉带来的奇异快感,让他彻底放弃了思考。
他只是一个被使用的器物,一个被打上烙印的所有物。而使用他、占有他、并以这种极端方式“宠爱”他的,是同一个存在。
当“野兽”终于满意地清理完毕,将那只湿漉漉、泛着红酒光泽和水光的脚轻轻放下时,李慕辰已经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睡吧,我的小荡妇。”
“野兽”将他打横抱起,走向卧室,声音里带着餍足的温柔,“明天……我们再继续。”
月光晾一下,李慕辰昏沉地闭上眼,任由自己沉入黑暗。
在这永无止境的闭环里,沉沦,是唯一的宿命。而他的身体和灵魂,早已习惯了这带着疼痛与羞辱的“宠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