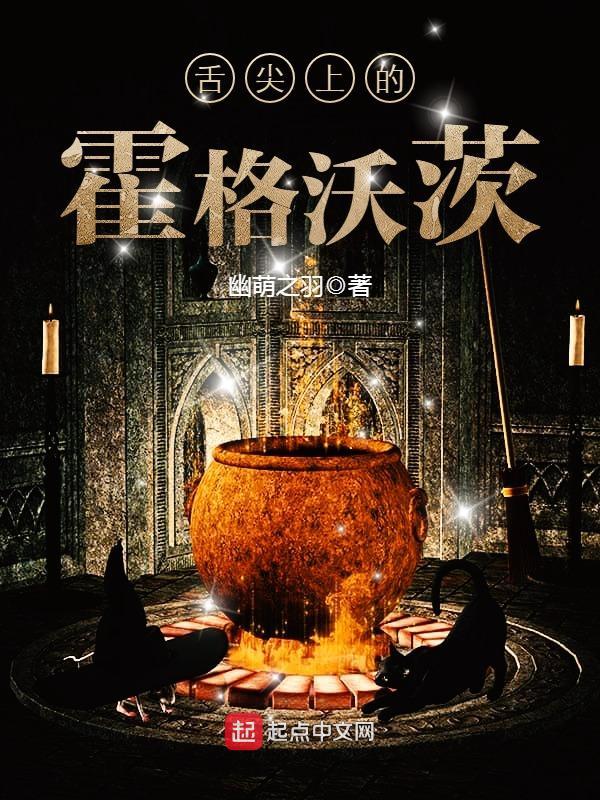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缝补人生阅读理解 > 4050(第5页)
4050(第5页)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但三两句话后,话又被陈蓦切了去。
“我……”
“我也是这次你爸来之后才突然想清楚的。”陈蓦说着,非常郑重其事的叫了蒋大佑的名字,“蒋大佑,我在意的,其实不是你不能在事业上跟我共进退,而是你要当主夫,要全身心的照顾家庭这件事情既不是出于你本身的热爱,也不是出于你对我和恩洱的爱,你是为了弥补你成长过程中的缺失,是为了为你妈妈正名,为了让你爸爸悔恨。我们这个小家,其实排到了很后面。”
蒋大佑听到这样的说法,条件反射性的想要去否认,可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说辞。
陈蓦继续,“记得吧?我们刚结婚时,我爸爸说让你跟原生家庭做好切割,原来我以为那切割是在你跟你爸之间,但现在想来,你更应该切割的,是你对你妈妈的深感遗憾。照顾家庭很有价值,可这份价值对我、恩洱我们这个家庭的惠及其实并没有这么大。”
剩下陈蓦还说了些什么,蒋大佑已听得不真切了,和陈蓦的种种以及远去的有关母亲的记忆跨越时空交织在一起,让他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失重感,仿佛周遭的一切都被颠覆了。
不知过了多久后,他才缓过神来,而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放在病床床头柜上的离婚协议书,蒋大佑抬手拿起,又看了看窗外让天色不明的阴天,终于下定了决心,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郑重其事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044人可以有执念,却不能只带着执念去过活
赵只今跟来雪来到蒋大佑的病房时,蒋大佑正泪眼婆娑的抱着离婚协议书伤神,听到门口传来的动静,他也没觉得丢人,泪珠反而更大更圆。
“怎么办?我好像是个‘妈宝男’。”他呜咽着道。
赵只今则首先注意到他拿着的离婚协议书,凑上前,往蒋大佑伤口上撒盐,“怎么?真离了啊?”
蒋大佑嚎的更伤心了,“你真是没有人性啊。”
来雪见状,送上了不如不安慰的安慰,“严格意义上来说,没领证之前,他们只是就离婚这件事达成了一致。”
蒋大佑:“……”
短暂的沉默后,他才想起关键点,“你们怎么来了?”
“你的准前妻嘱咐我们来看看你。”赵只今说着坐到了床边,环望了下病房后,回忆忽然攻击了她,“真想不到,有天我们竟又齐聚一间病房,只是上次是我跟来雪躺在那儿。”
*
过隙白驹,初识时,这三人只十八九岁,在小小的象牙塔里打转,人生的篇章还未完全打开,而今已过了六七年,赵只今短暂成功快速破产,来雪从天之骄子沦为许多人口中的‘高学历废物’,蒋大佑结婚生子又将要离婚……
“我感觉,人生很漫长看不到尽头,又觉得好像过了大半辈子。”赵只今感到矛盾的感慨。
蒋大佑也叹气,“我也有种过了大半辈子的感觉,只是……没过好。”
来雪没跟着发言,打乱了队形,前两人等不到她说话,一齐望向了她,目光炯炯。
来雪哼一声,道:“别提从前,那次要不是你们,我就能见到……”
她在关键时刻急刹车,不愿再吐露,赵只今却忍不住不问,“就能见到谁?”
来雪闭口不言,赵只今被心事卡住了好几天,以为今晚必须要来个真心话局,于是摸出手机,提议,“不如我们先喝一杯?”
外卖小哥很快将酒送来,赵只今扛着一提啤酒上楼时,很怕被医生或护士发现,直接把酒丢出大门去。
不过后面证明,有时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蒋大佑端着罐根本没打开的啤酒,立马便进入了微醺状态,他缓缓地道出了对母亲早逝的不甘,以及他对母亲离开后父亲态度的执念。
“我爸瞧不上我妈,觉得她不工作,整天就为着家里转,跟不上他的步伐,那我就干脆成为我妈那样的人。”蒋大佑说着,苦笑里又带着些羞涩,“不遑多让的说,我如果不搞叛逆,就算够不上清华,应该也是能够上北航的。”
认识这么些年,蒋大佑第一次没再用《下一站天后》的歌词去粉饰他主夫梦想背后的心酸与不忿,赵只今跟来雪听了都是沉默良久。
蒋大佑在倾诉过程中也多少开解了自己,“陈蓦说得对,
人可以有执念,却不能只带着执念去过活。”他深深叹了口气,决心要先从这份执念中抽离出来。
来雪在听到‘执念’这一词时,眉头深锁,在这一点上,她倒跟蒋大佑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她以为,于某些人而言,执念是一种不可失的牵引,让晦暗不明的人生有了些许盼头,而巧合的是,她的执念,亦是和一个人挂钩。
跟蒋大佑的些许相似终于让来雪有了些许吐漏心事的欲望,她晃了晃半空的啤酒罐说:“认识那一年,我报名参加北京电影节的志愿者选拔,是为了见到奚美娟。”
赵只今有些吃惊,“追……星吗?”
来雪点点头,“算是吧,替我阿嬷追星。”
“阿嬷?”
“就是姥姥。”来雪解释,而后又说:“我会做陪诊,也是因为我姥姥,因为我很遗憾,在她弥留之际,我没能陪伴在她左右……嗯,这么说不太准确,准确说来,我甚至都没能探望她哪怕一次。”
“怎么会?”
“那年我高考。”
“啊……这……”
“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