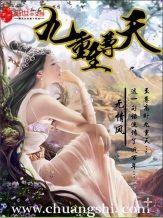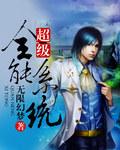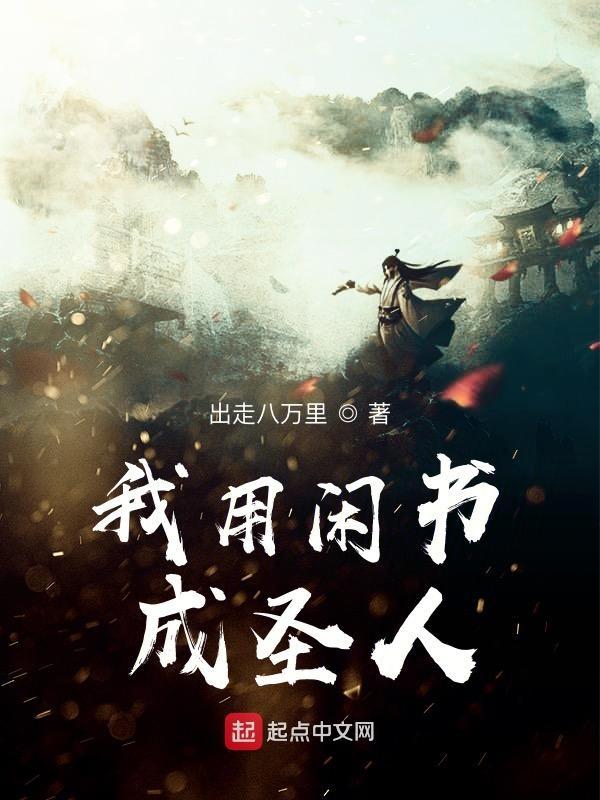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华娱从捧红大田甜开始 > 第23章 衝击春节档(第2页)
第23章 衝击春节档(第2页)
彼时,电影刚传入中国不久,人们仍基本维持著农历新年前后几天休整歇息的习惯,商家歇市,演出行业也会“封箱”。
基於这一习惯,最初的国產片一般在首映时会有意避开农历新年中人们“忙年”“拜年”最核心的几日。
包括前些年,影院也都是在过年期间几乎不开门。
不过近些年在春节前后上映的影片越来越多,所以春节期间影院也都是开门营业的。
只不过彼时春节上映的影片,还算在贺岁档里面。
彼时的中国电影市场对春节档还没有形成概念,因此,春节期间上映的电影並未有特殊的宣发和营销,票房收益不到4亿元。
真要等春节档“独立”出来,成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档期。
那还得2013年,《西游·降魔篇》的出现,以12。46亿元的总票房掀起了全民观影热潮,由此,春节档正式崛起。
“春节看电影”逐渐成为当今时代的新民俗,大家藉由电影聚在一起,聊在一起,创造共同的回忆与情感。
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在春节期间进行文化消费的欲望,同时也为集体社交活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仪式化纽带。
顾璟恆自然不能等到2013年以后,吃周星星带来的红利。
冯裤子既然能够靠著內地第一部贺岁档电影《甲方乙方》,让“贺岁档”的概念逐渐成形。
那顾璟恆为什么不能,提前靠著《人在囧途》,逐渐打造出春节档的概念。
“春节档?”
陈止希指尖在剧本封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眉头微蹙,“现在影院春节排片量还不到平时的三成,观眾也没这个习惯——大年初一揣著票根去影院?家里长辈怕是要骂『不务正业。”
顾璟恆没直接反驳,从抽屉里翻出一叠数据报表推过去。
最上面是近三年春节期间的城市票房统计,曲线虽然平缓,却能看出每年都在以15%的幅度往上爬。
“去年大年初三,二线城市的上座率超过了平日的五成。”
他指著其中一行数字,“不是没人看,是没人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温牧野翻到剧本里李成功在火车站给家人打电话的段落,忽然抬头:“我前年春节没抢到票,在出租屋里看春晚重播,楼道里全是別家的鞭炮声。”
他顿了顿,“要是当时有部讲春运的电影,我肯定会去看。”
“就是这个理。”顾璟恆打了个响指,“春运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挤火车、赶汽车、大包小包的行李,这些细节往银幕上一放,观眾就会觉得『这说的是我。春节档缺的不是观眾,是能让他们產生共鸣的故事。”
陈止希沉默片刻,忽然翻开公文包,抽出一张空白的宣发计划模板。
“40天拍完,后期要压缩到两个月內,意味著特效和剪辑必须同步推进。”
她笔尖飞快地写著,“宣发得提前一个月铺,重点打『过年回家的情感牌,联合火车站做线下活动——比如给排队买票的人送电影海报。”
申奥凑过去看,忽然拍了下手:“还可以找那些拍春运纪录片的媒体合作!他们手里有现成的素材,剪个混剪预告片,真实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娜扎一直没说话,这时忽然小声说:“我去年跟妈妈去亲戚家拜年,路上堵车堵了三个小时,我妈念叨了一路『还不如在家看电影。”
她抬眼看向顾璟恆,“说不定真的有人不想走亲戚呢?”
顾璟恆笑起来,把剧本往中间推了推:“所以,咱们要给他们一个不去走亲戚的理由。”
陈止希的钢笔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温牧野在剧本上標著重號,娜扎悄悄给每个人的杯子里添了热水。
没人再提“仓促”两个字。
他们都知道,要在一片空白里造出一个新档期,靠的从来不是时间充裕,而是能不能抓住那个藏在千万人记忆里的共鸣点。
“那就这么定了。”
他拿起笔,在剧本扉页写下“春节档”三个字,“让观眾知道,春节除了拜年和饺子,还可以有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