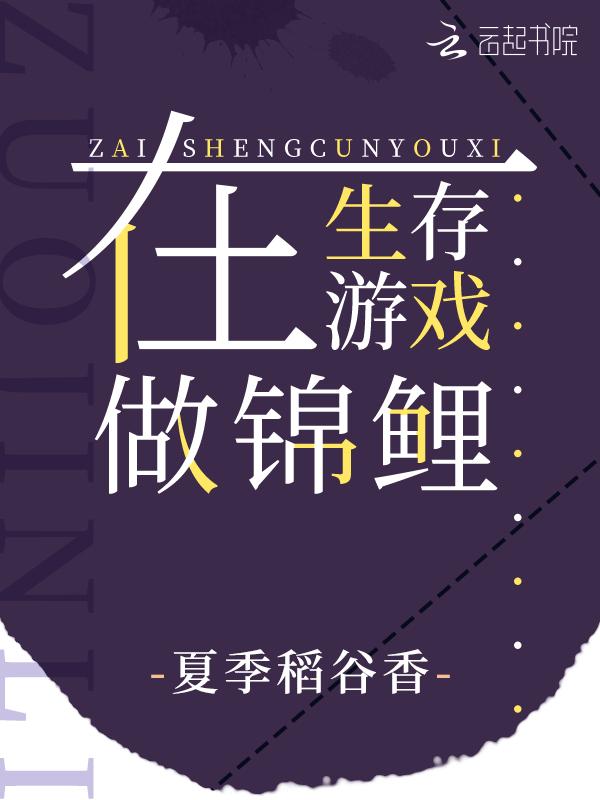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安坏坏离开才是真正开始 > 第8章(第2页)
第8章(第2页)
技师把一副耳塞放进她耳朵,又用小枕头固定了她的手臂。
随着床板缓慢推进机器内部,她眼前的光线一点点被遮住,只剩下顶部那圈圆形开口,像是个遥远的舱门。
空间变得局促,只有30厘米不到的垂直距离让她感觉被什么压住了胸口。
接着,声音来了。
金属般的敲击声重重地砸在耳边,像工地上的打桩机,断断续续、毫无节奏。
每一种不同频率的震动,都像是有东西在她头骨里轻轻震颤。
她闭上眼,试图不去注意那些响声。
时间变得缓慢,像是在计时器里一秒一秒滴落。
她数过:四组声音、一段停顿,又四组声音,重复循环。
每一组都比前一次更沉重。
她的肩膀开始发酸,但不敢调整姿势。
耳朵里除了机器的轰鸣,还有自己隐隐的心跳声。
十几分钟过去,有人说话的声音透过耳机传来:“现在准备注射增强剂。”她感到一阵凉意从手背上的静脉注射口推入体内,过了一会儿嘴里浮起一股金属味,微弱却清晰。
接下来的几分钟更像是等候结束的倒计时。声音依旧,姿势依旧,空间依旧狭窄,曾荻觉得越发难熬。
终于,床板开始慢慢后退。光线一点点回到眼前的世界。
“可以起来了。”技师摘掉固定器,把她从床上扶起来,“检查做完了,片子等两个小时去自助机上取。”
曾荻坐起身,揉了揉僵硬的肩膀。
整个过程无痛,却极度安静、漫长而机械。
走出检查室那一刻,她感觉像刚从一个没有时间的盒子里出来,意识缓慢地回到真实。
等报告的时间里,曾荻给自己买了杯咖啡。
咖啡的味道实在平平无奇,甚至都没什么香气。
但她还是抿了一口。
嘴唇触到杯沿的瞬间,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太渴,只是需要一个动作让身体安静下来。
等待体内某种结果的感觉是一种说不出的迟钝和飘忽。
明明她刚从机器里出来,可仿佛脑子还在那密闭的磁共振舱里,一圈圈扫描还在无声地进行。
她的手腕还留着注射针按压后的痕迹,皮肤冰凉。
她在角落找到一张靠窗的椅子坐下,把咖啡放在小桌上,两手搓了搓,试图恢复一点温度。
大厅里不时有人路过,有人轻声交谈,有人抱着片子走出诊室,神色各异,或轻松、或沉重。
她看着这些来来去去的身影,突然生出一种微妙的抽离感。
她想起刚才机器里的声音,像是从地下深处传来的信号,又像是某种她听不懂的语言,在她脑中留下了隐约的回响。
两个小时的时间很漫长。
曾荻期间去自助机上扫了好几次单子。急切的心情像是在等什么审判结果。
终于。
曾荻第三次排队扫码,片子缓缓地从机器里传输出来。
曾荻看不懂。
那是那是一组泛着冷光的黑底胶片,密密麻麻的影像,每一张都是脑组织的截面图。
那些灰白色的轮廓,环环相套,有时是对称的,有时却似乎有一点偏斜。
她拿起片子,回到神经外科的门诊室。
王主任拿起片子,依次浏览,指尖有节奏地翻动着那些黑底灰影的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