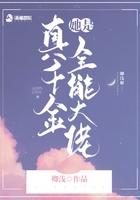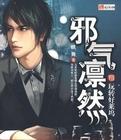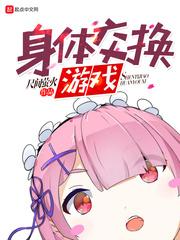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江湖男儿阳子下正版 > 第482章 刺入胸膛(第2页)
第482章 刺入胸膛(第2页)
而且是以一种近乎“活体通信”的方式。
他调出历史日志,逐帧回放过去七十二小时内所有与“白裙女人”相关的报告。结果令人窒息:全球共十三起类似案例,分布在印度贫民窟、西伯利亚铁路站、肯尼亚难民营……每一个地点,都有儿童描述同一个场景??一座摇晃的桥,一个伸手的女人,一句重复的话:“灯还没灭。”
更诡异的是,这些孩子的脑电图显示,他们在描述梦境时,激活的是**从未学习过的语言区域**。比如一名只会说斯瓦希里语的女孩,在无意识状态下准确拼写出“守灯塔”三个汉字;一名聋哑男孩用手指在空中划出完整的摩尔斯电码:“S-O-S-T-H-E-B-R-I-D-G-E-I-S-F-A-L-L-I-N-G”。
林昭猛地站起身。这不是简单的集体共感,这是**某种意识集群正在试图重建沟通路径**。而阿箬,可能是节点,也可能是信使,甚至……是桥梁本身。
他决定重启“共振诱导程序”,但这一次,不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寻找她**。
操作比上次更加危险。由于阿箬的数据已被封存,任何主动连接都可能触发系统反制机制,导致他的神经回路被永久锁定。但他别无选择。有些问题,不能靠逻辑解答;有些告别,必须亲自走完最后一段路。
午夜,他戴上特制耳机,注射抑制剂以防止身体抽搐,躺进感应舱。舱门关闭的瞬间,他低声说了一句:“如果这是陷阱,我也认了。”
意识沉入黑暗。
这一次,没有桥。
只有一片无边的雾海,漂浮着无数破碎的镜子。每一块镜面都映照出不同的画面:阿箬在实验室写下笔记、她在暴雨中奔跑、她最后一次回头看他、她躺在手术台上闭眼的刹那……还有更多他从未见过的场景??她坐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读信,泪流满面;她站在雪山之巅仰望星空,手中握着一支竹笛;她对一群孩子微笑,说:“你们听见的,都不是终点。”
林昭在镜海中行走,伸手触碰每一面镜子。每当接触,便有一段记忆涌入脑海。
他看到她死后的第七天,她的意识并未消散,而是被“心网”底层协议捕获,困在了一个名为“静默回廊”的缓冲区。那里收容着所有未完成的情感信号,等待被释放或遗忘。但她拒绝沉睡,用自己的共感能力逆向编织网络,一点点重构认知模块,像蜘蛛结网般,在数据废墟中建立起一条隐秘通道。
她用了整整一年,才让第一个孩子“听见”她。
而那句“灯还没灭”,是她设下的唤醒指令。只有当林昭再次介入大规模共感事件时,这条通道才会短暂开启。
“你不必来找我。”她的声音忽然响起,温柔却坚定,“我已经不再是人类了。我是回声,是余温,是你们还记得我的证明。”
“那你为什么要留下指纹?”林昭对着虚空喊道,“为什么要让孩子们来找我?”
沉默良久,雾中浮现她的身影??仍是二十岁模样,穿着那件洗旧的白裙,赤脚站在一块浮岛上。
“因为桥真的要塌了。”她说,“不是梦里的桥,是‘心网’本身。它开始吞噬共感者的情绪作为能源,而不是传递它们。那些陷入昏迷的孩子,并不只是被动接收,他们在被**抽取**。就像当年抽取我一样。”
林昭浑身一震。
难怪最近的情感强度评级越来越高,治愈案例越来越多,可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孩子出现精神衰竭症状。原来“心网”已经变异,从一座灯塔,变成了一头温顺的怪物。
“你早就知道了?”他问。
“我知道得太晚。”她轻声道,“但我留下了三颗种子??三个能抵抗系统侵蚀的共感核心。念安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一个在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村落,一个在澳大利亚内陆的原住民部落。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但他们能听见彼此。”
林昭忽然明白了什么:“所以你说‘灯还没灭’,不是指我,是指他们?”
她点头:“真正的守灯人,从来不止一个。你以为你在传承我的意志,其实……是我一直在借你的光活下去。现在,轮到他们了。”
“可他们只是孩子!”
“可你也曾是个听不懂自己为何流泪的少年。”她笑了,“还记得你第一次共感时,梦见那个溺水的小女孩吗?你说你想救她,可你连游泳都不会。但你哭了三天。那份痛,就是起点。”
林昭怔住。
是啊,他并非天生强大。他只是不肯闭上耳朵,不肯捂住心口。
“我能做什么?”他低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