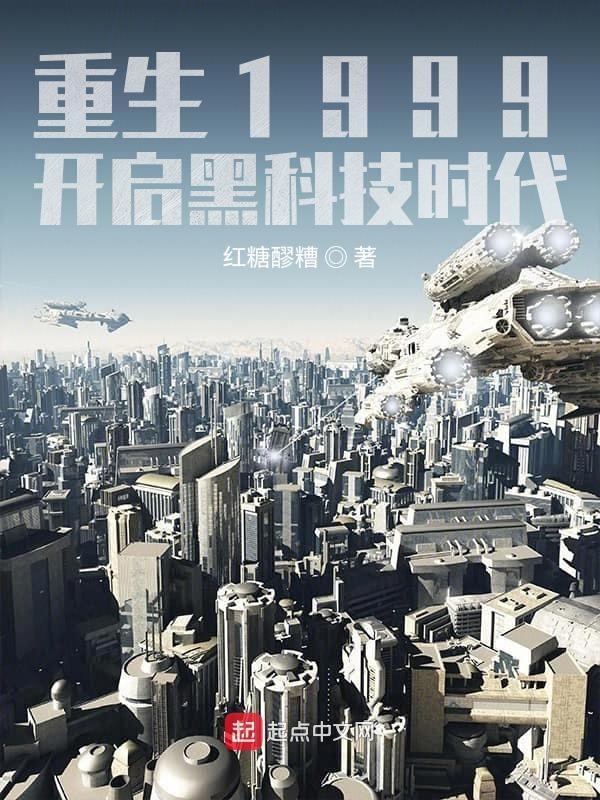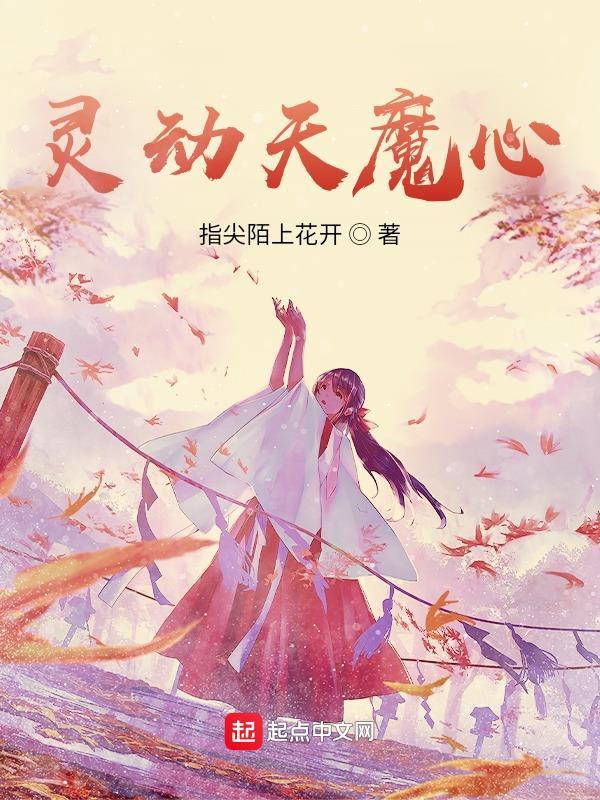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妻子浪翻了免费完整版 > 第1402章 何雅的告白(第2页)
第1402章 何雅的告白(第2页)
她说的是:“等你来接我。”
我的心骤然收紧。
紧接着,车子驶入弯道,轮胎打滑,失控翻滚。画面颠倒旋转,最后定格在破碎的挡风玻璃外飞速掠过的树影。
视频结束。
我反复回放那句话,一遍又一遍。不是“我爱你”,不是“对不起”,而是“等你来接我”。
她知道我会追上去。
就像灵魂湖边的那个幻象,不是偶然,不是幻觉,而是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丝执念的投射??她在等我完成告别。
我走出咖啡馆,阳光刺眼。街道喧嚣,人群匆匆。我站在十字路口,突然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当晚,我拨通了张野的电话。
“你还记得我们在格尔木找到的那辆残骸吗?”我问。
“当然记得。烧得只剩骨架。”
“我想再去一趟。”
他沉默片刻:“你现在状态……没问题吧?”
“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我说,“有些路,必须亲自走完。”
一周后,我们再次踏上西行列车。张野请了十天假,林茜托朋友安排了当地向导。这一次,我不再是为了寻找安宁的存在,而是为了确认她的离去。
高原依旧荒凉,风沙呼啸。当我们抵达事故地点时,那里已长出稀疏的绿草,几株野花在石缝间摇曳。警方早已撤走所有标记,只留下一道浅浅的刹车痕,被雨水冲刷得几乎看不见。
我蹲下身,用手轻轻拂过地面。
“就是这儿。”张野站在我身后说,“当时车翻下去三十多米,撞在岩石上。救援队花了六个小时才把人抬上来。”
我点点头,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我在海边埋下的那枚婚戒,以及一张我和安宁的合影??是我们结婚三周年那天拍的,她在游乐园门口踮脚亲我,笑容灿烂得像个孩子。
我把盒子放进坑里,覆上土,插了一根木棍当墓碑。没有刻字,不需要名字。这里埋葬的不是尸体,而是一个男人用了三年时间才终于肯放手的记忆。
“你打算写进书里吗?”林茜轻声问。
“会。”我说,“但不会写得太痛。我要让读者知道,爱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守着灰烬不放。有时候,最好的纪念,就是好好活着。”
回程途中,我在火车上打开笔记本,写下新的章节:
>**“当一个人选择死去,她带走的不仅是生命,还有你对未来的所有想象。而当你终于学会带着这份空缺继续前行,你就成了她留在人间的最后一束光。”**
到家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人是出版社的编辑,附带一份合同:《我死后,妻子浪翻了》即将加印,并计划改编为广播剧。同时,多家媒体希望采访我。
我婉拒了所有节目邀约,只同意接受一家独立杂志的文字专访。记者问我:“您认为安宁的‘出现’,是心理现象,还是超自然存在?”
我回复:“我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不是她是否真实存在于物理世界,而是她曾真实地活在我的心里。而现在,我允许她离开了。”
采访发表那天,我去了图书馆。在一楼的心理学区,我看到了自己的书摆在推荐架上。封面是黑白照片:一双男人的手正缓缓松开一枚戒指,背景是晨雾中的湖泊。
一个小女孩站在旁边,仰头看着书名,问妈妈:“爸爸也会这样想念妈妈吗?”
那位母亲摸了摸她的头:“如果你爸爸足够爱你妈妈,就会。”
我默默走开,眼角湿润。
生活渐渐回归日常节奏。我正式复职于心理援助中心,每周主持两次团体辅导课。第一次上课前,我站在讲台前,看着底下那些眼神黯淡的人们,忽然开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