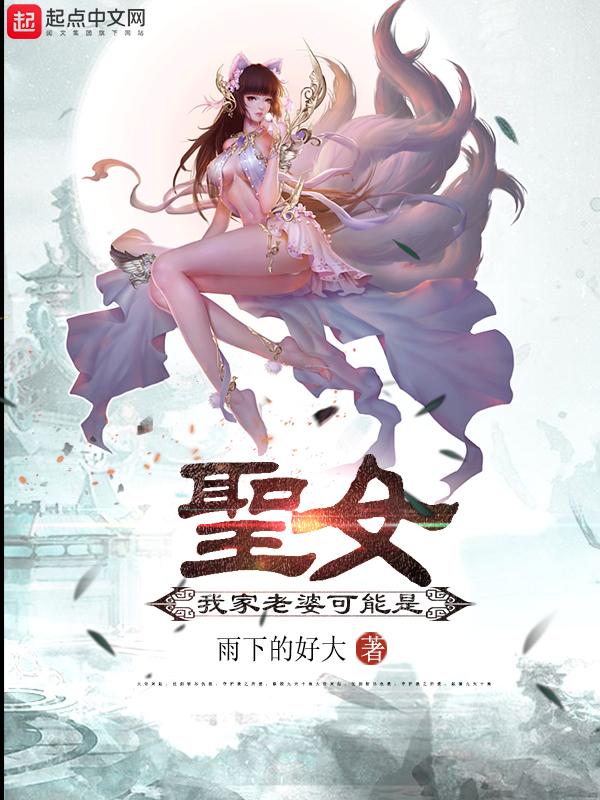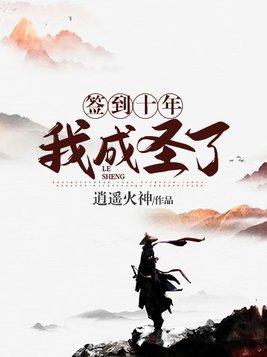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穿越者不死于遗忘 424242 篱笆好网 > 第一百二十四章 无限善循环公式(第3页)
第一百二十四章 无限善循环公式(第3页)
>其名不可呼,然其声常在风中。”
消息传出,共忆网立刻将其纳入“远古共鸣库”,并触发自动联想机制。结果令人震惊:这段文字的语义结构,竟与现代共忆网底层协议高度相似,尤其是关于“情感密度加权传播”的算法逻辑,几乎完全一致。
难道早在数千年前,人类就已经掌握过这种记忆传承的技术?
更不可思议的是,当研究人员尝试将这段岩画扫描件上传至共忆网时,系统竟自动匹配出一段丢失多年的音频??来自林远早年在西北考察时的野外录音。他在风中说:
>“我一直觉得,共忆网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只是……重新学会了怎么使用它。”
那一刻,许多学者开始怀疑:或许所谓“文明进步”,从来都不是线性向前,而是不断回归那些被遗忘的初心。
---
盛夏再度降临,西南山区的公路旁,一位老人坐在桥墩阴影下乘凉。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腿边放着一只破旧帆布包。过往车辆很少,偶尔有骑行者经过,会停下来问他要不要喝水。
他总是摇头,微笑。
没人认出他是陈默。
他已经七十岁了,走路更加跛,听力也开始衰退。但他每天仍坚持巡视这段由他亲手修建的山路。他说这条路通向的不只是村庄,还有“那些走丢了却还在被人记得的人”。
傍晚时分,一群高中生来这里写生。他们听说这里有位“沉默的修路人”,便想画下他的肖像。其中一个女孩鼓起勇气上前:“爷爷,我能为您画张画吗?”
陈默看了看她手中的素描本,点点头。
她认真地画了起来,笔尖沙沙作响。画到一半,她忽然问:“您是不是认识林远老师?”
陈默的手顿了顿。
良久,他轻声说:“我们是同事,也是兄弟。”
女孩眼睛亮了:“我在课本上学过他的事!他说,只要有人记得,他就没死。”
陈默笑了,眼角皱纹舒展开来:“他说得对。”
她继续画,完成后递给他看。画中的他坐在夕阳下,背景是蜿蜒山路,头顶上方,漂浮着一朵虚幻的蓝铃花。
“为什么画这个?”他问。
“我觉得,”她仰起脸,“您守护的不只是路,还有他留下的光。”
陈默接过画,仔细看了一会儿,从包里取出一支旧钢笔,在画纸角落写下一行小字:
>“他也在这条路上,走得比我慢一点。”
然后,他把画还给她:“送给你吧。但答应我,以后每年春天,都画一朵蓝铃花。”
“好!”女孩用力点头。
夜幕降临,学生们离去。陈默独自坐在原地,抬头望向星空。今晚没有极光,也没有信号波动,只有银河横贯天际,静谧如初。
他掏出那台早已报废的终端,轻轻摩挲着外壳上的划痕。他知道,它再也无法启动,但它承载的东西,早已流入世界的血脉。
他闭上眼,低声说:
“老林,孩子们还在讲你的故事。”
风穿过山谷,吹动树叶,发出沙沙声响。
像是回应。
又像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