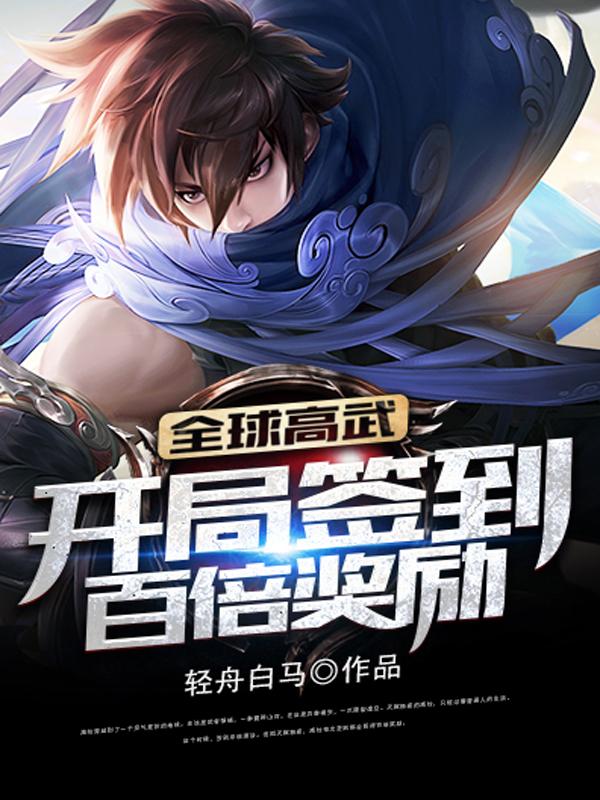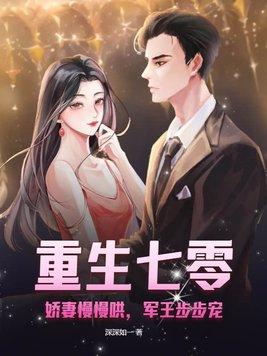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掏空祖宅嫁军少宠疯了 笔趣阁 > 第341章 怎么救情敌(第3页)
第341章 怎么救情敌(第3页)
秋天,阿阮收到一封特殊来信。寄件人是阿富汗那位战地记者创办的心理援助中心,附有一段视频??十几个孩子围坐一圈,每人手中拿着一张画。他们轮流讲述自己画中的亲人:有的画母亲做饭,有的画父亲修车,有的画妹妹扎辫子。最后,老师引导他们把画折成纸船,放进院中水池。
镜头扫过水面,每只纸船都载着一片银蓝花瓣,缓缓漂向中央。突然,所有花瓣同时升起,在空中拼出一个巨大的“安”字,持续数秒后消散。
视频末尾,孩子们齐声用中文说出一句话:
>“我们学会了,好好说再见。”
阿阮看完,久久不能言语。她回信只写了五个字:“你们做得很好。”
冬雪降临之夜,她再次梦见图书馆。这一次,她不再是读者,而是写作者。无数空白书页在她面前展开,她提笔写下一个个名字:陈默、林晚秋、李阿婆、玛尔塔、陈芸、林昭、老兵、母亲、女儿、陌生人……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浮现一段人生片段,一段释怀的瞬间。
当她写完最后一笔,整座图书馆轰然化为光雨,洒向大地。她听见无数声音交织成歌:
>“我不再等你回来。”
>“因为你从未真正离开。”
>“我好了。”
>“我们都好了。”
她猛然惊醒,窗外大雪纷飞。她披衣起身,走到院中。雪地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串脚印,从大门一路延伸至水缸边,又折返回去。脚印很轻,像是怕惊扰梦境。
水缸中,漂着一只新的纸船,船上压着一片干枯的樱花标本??正是她童年丢失的那一片。
她拾起它,贴近胸口,感受到一丝温热。
次日清晨,樱园广播准时响起。虽无声音,但所有在场之人皆觉心头一震,仿佛听见了什么。监控显示,那七分钟里,井底晶体层释放出一道脉冲信号,经分析,竟是由全球历年积累的“释怀时刻”压缩而成的信息流。
科学家称之为“人类心灵的第一次集体低语”。
而孩子们只是笑着说:“听,风在唱歌。”
又一年春分,阿阮拄着拐杖走入樱园。她已八十二岁,步履蹒跚,眼神却依旧清明。她站在井边,看着玻璃罩开启,等待那一片银蓝花瓣。
花瓣如期而至,落在她掌心,化作光点渗入皮肤。她闭眼,耳边响起母亲的声音:
>“现在轮到你帮我放下了。”
她微笑,轻声回应:“好。”
同一时刻,江南老宅的铜铃再度响起,清越悠扬,传遍十里村落。屋檐下,那只布偶兔风筝又一次掠过天际,牵线的孩子回头一笑,眉眼竟与幼年阿阮一般无二。
风起了。
樱花纷纷扬起,如雪如歌,洒落人间。
有些人走了,但他们教会我们如何停留。
有些人留下,却学会了怎样飞翔。
这世上最深的爱,从来不是抓紧,而是轻轻松手??
然后对着风说一句:算了。
那便是永恒的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