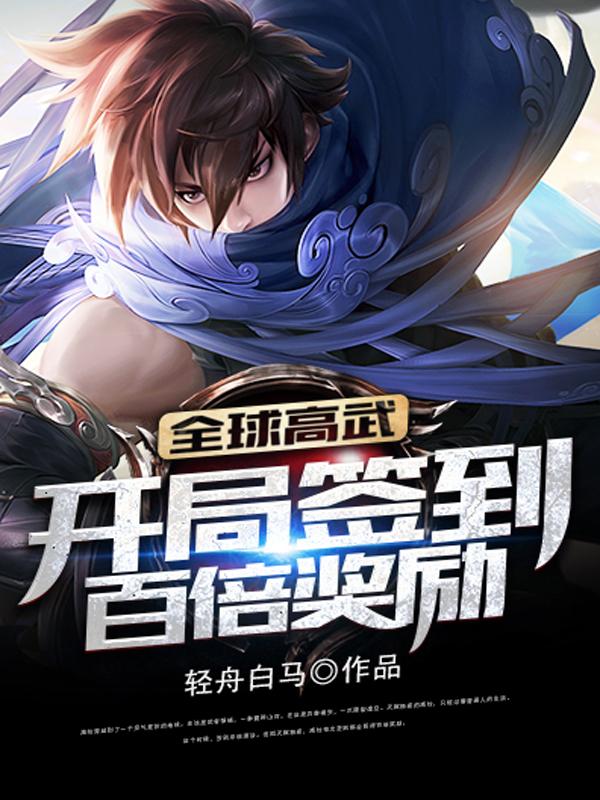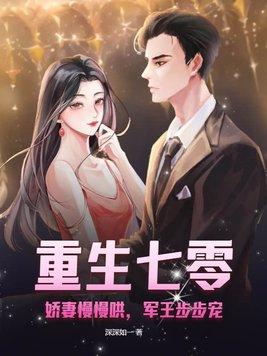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梦千年之恋歌词 > 暗涌(第1页)
暗涌(第1页)
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已入吐蕃,此时大唐的朝堂上开始涌现一股新的纷争。
太子李承乾时年二十二岁,作为李世民的第一个孩子,他自小备受关注亦被寄予厚望。幼时勤勉好学,尊师敬长,一直深得朝臣赞誉,不幸贞观十三年罹患足疾,自此性格逐渐叛逆,于是李世民“搜访贤德,以辅储宫”,先后挑选了十余位老臣、名臣出任东宫辅臣,然这些老臣言辞尖锐,不仅未能使太子重塑德行,反而让太子愈发任性。
与此同时,嫡次子李泰却宠冠诸王,他爱士好文,工于草隶,集书万卷。李世民允许李泰在魏王府开设文学馆,自行招引学士。
贞观十六年二月,魏王与众文学馆学士完成《括地志》编纂,四海版图、州县疆界、山川河流、物产民俗,皆有详载。朝堂之上,李世民亲自过目卷册,眉眼间带着难掩的欣慰——天下大事,终于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当即赐以重金以作嘉奖。
我在安国府中得知此事,心中暗暗叹息:一场兄弟相争的较量即将展开,即使我出言劝阻陛下莫要过度宠爱魏王,最终也依然不会改变此事结局。若置身事外,不发一言,也无法避免李世民的召问。
思考良久,终于放下,
罢了,我决定听从自己的内心,若李世民想问便尝试一劝。
初夏,太极宫内,晨光照着金色的丹陛。风从宫阙深处吹出,卷动檐角的风铃。
早朝后众臣退下,独留太子与魏王立于殿下。
李承乾身着玄服,神色拘谨,却隐隐有怒气压抑在眉间;
李泰则一身青袍,面容温润如玉,唇角带着不卑不亢的笑。
“承乾,”李世民的声音低沉,却带着压抑的怒意,“你身为太子,素号仁孝,近来却荒于学业,疏于政理。连师傅数次上奏,你亦不省思?”
太子的声音有些颤,却透着倔强:“儿臣并非不学,只是……魏王所为,父皇皆赞。儿臣若有片言不合,反被斥责,实难心平。”
片刻沉默后,李世民冷笑一声:“平?天下岂容一人以‘平’字为由行怠慢之事?你心中若真有不平,不该怨人,只该怨己。”
李泰的声音,温润柔和,却带着一点似是无意的谦辞:“太子之言,臣弟不敢当。父皇夸臣弟,不过小事。天下大计,非臣弟所能妄议。”
那语气,恰到好处——既谦逊,又像在无声提醒。
李世民低声道:“朕知你才识过人,《括地志》一书,劳苦功高。然你与太子,乃一母同出,怎能暗生嫌隙?”
“儿臣不敢。”李泰答。
空气凝固。直到传来一声沉响——李世民起身,衣袂扫过案几。
“承乾、李泰——你们皆为朕子,朕欲教你们和睦共处,而非相争。若有一日,兄弟阋墙,骨肉相残——即便社稷无恙,朕亦无颜见你母后!”
那一句“你母后”,带着太多情绪——愧疚、哀伤,还有一丝被岁月磨钝的痛。
殿内静默。良久,只听李承乾压抑的声音:“父皇……儿臣知错。”
李泰也随声附和:“臣弟亦知。”
门缓缓开启,二人齐出。
早朝结束后。李世民以商议西突厥内乱之事的理由宣我入宫。
我由内侍引入甘露殿,行礼后问道:“陛下今日召臣前来,可是有要事想问?”
他没有立刻回答,只缓缓转身。那一瞬间,我看到他眼中藏着疲惫与犹豫——那不是皇帝的神色,而是一个父亲。
“卿可听闻……太子与魏王之事?”
我垂首,轻声答道:“臣有所闻。”
殿中一时寂静,只听得烛火微微炸响。烛火映着他鬓角的白发,那一抹银光让我心中微痛。
“承乾……是朕的长子。”
他叹息,“承乾年少时聪慧纯良,吾与皇后常慰,谓社稷可托。然而如今……失德、失度,近佞远贤。朕原以为扶之以老臣,能稳其性,谁料反令其怨朕。”
我沉默。
“而李泰……”他语气微顿,眼底闪过一丝自责,“魏王才学出众,朕不过是一时欣慰,赏了几句夸言,岂料他竟因此自矜,意动储位。”
我抬起头,迎上他那双深沉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