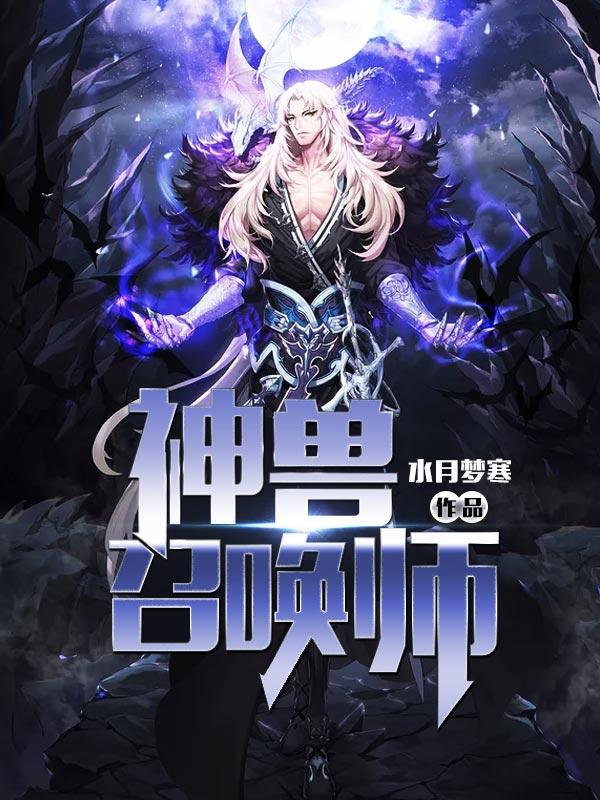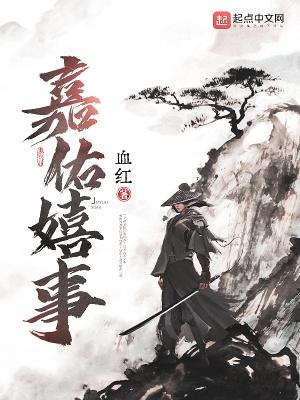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梦千年板材 > 终章(第1页)
终章(第1页)
贞观二十二年春,长安的天色依旧明亮,
然而那一年的风,却有了不祥的静。
房玄龄病重的消息自弘文馆传来时,李世民沉默了许久。
案上摊开的奏表,他未读,笔却一直握着。
那笔锋微颤,墨迹一点一点渗开,如同他心中隐隐的痛。
三日后,他亲往探视。
病榻前,房玄龄气息微弱,已无往日的镇定风度。
但见君至,仍挣扎着下榻行礼,被李世民亲手扶住。
“卿病已重,不必多礼。”
房玄龄笑了笑,声如细丝:
“臣……此身无用矣。但闻陛下仍思再征高句丽,臣惶恐不安。百姓甫得休养,陛下之盛业已定,何必更以劳师动众?臣虽病中,仍愿谏止。”
李世民凝望他,眼中光色复杂。
这一刻,他不是帝王,只是失友的人。
“卿自贞观初随朕至今,凡大事皆与谋。
今卿病笃,却犹忧国——贞观之柱,舍卿其谁?”
房玄龄颤声答:
“贞观之盛,不在臣。在陛下能听忠谏,抑己安人。臣去之后,愿陛下慎言慎行,毋忘贞观之初心。”
说完,气息微断,泪湿枕边。
李世民垂首,不语良久。
六月一夜,房玄龄在烛光中昏昏而逝。次日,朝堂传旨,举国致哀。
李世民亲书谥文,落笔时泪滴于纸上,化开墨痕。
“玄龄,朕之臂也。臂折,则心伤。”
那夜,他独坐含光殿,
旧臣姓名浮现心头:杜如晦早逝,魏征先亡,长孙皇后远去,如今又失房玄龄。
贞观旧人,一个一个散入尘烟,
昔日议政的弘文馆,如今空空如也。
我立在烛后,轻声道:“盛世终将有人谢幕。”
李世民缓缓抬头,目光穿过烛火,看向我:
“卿说得是。盛世不亡于外敌,而亡于岁月。
朕所筑之唐,不过一段流光。光在,影在;光灭,影亦无存。”
我听得心酸,却无言,只为他添衣。烛影在地上重叠、拉长,像极了那些逝去的名字——在盛世之光里,一点一点,淡入永恒。
贞观二十二年七月,李世民病重,召玄奘讲授《仁王经》,我立侍其侧:
病榻前,玄奘法师合掌立于灯下,衣袍简素,眉目澄明。
他诵《仁王经》之偈,声若清泉:
“若王持国,以正法治,则国安;
若以嗔心治国,则民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