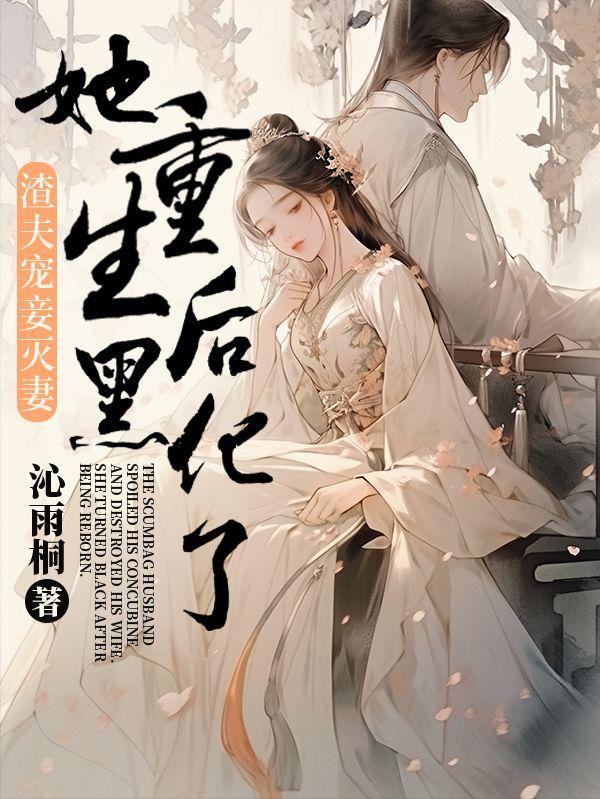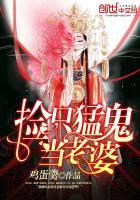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太子原创女主 > 太子(第1页)
太子(第1页)
夜色深沉,潇湘馆内烛影摇红。
黛玉伏在案上,呼吸渐渐均匀,意识仿佛脱离了躯壳,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悠悠荡荡,再次沉入那片无边无际的迷雾。
不知过了多久,迷雾缓缓散开,只见一座精巧的水上楼阁显现于前,飞檐反宇,朱栏玉砌,四面轩窗敞开,垂着轻纱,阁外是一池碧水,在朦胧月色下泛着鳞鳞银光。
黛玉心中疑惑,这景致清雅别致,却全然陌生,绝非她平日所思所能幻化。
她步入水阁,只见内部陈设清雅,一张紫檀木榻临窗放置,榻上倚着一人,正望着窗外池中几株残荷出神。
黛玉犹疑间,那男子仿佛感应到什么,缓缓转过身来。
四目相对的刹那,黛玉呼吸一顿。
是他!那个在她梦中出现的男子!
只是此刻的他,与上次已大不相同。那时只窥见他双目无神,不曾看清面容,如今细观,虽病容未褪,却愈发显得眉目清隽如玉,那双眼睛,如同被秋水洗过一般,冷冽中透着清亮,此刻正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惊,直直地望向她。
这般对视不过瞬息,却让明昭心神俱震。
比起上次梦境中那个模糊的幻影,此刻的神女清晰得令人心惊,不是庙宇中宝相庄严的金身塑像,也不是壁画上华彩熠熠的天女模样。
她立在光影交界处,身形清减得像是月光凝成的影子,仿佛下一刻就要随着夜风散去。
几分来不及掩饰的慌乱,几分与生俱来的清冷,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悲悯,让她看起来既遥远又真切。
这一刻,什么仙凡之别,什么宫廷礼仪,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明昭眼中只剩下这个如梦似幻的身影,生怕一个眨眼,她就会化作月光消散。
黛玉被他看得心慌意乱,她下意识地后退半步,想要躲进水阁外的迷雾中。
“请留步!”
明昭急急出声,声音因激动而略显沙哑。他试图撑起身子,动作间牵动了未愈的伤病,微微蹙了下眉,但目光始终未曾从黛玉身上移开。
“神女……”他的语气小心翼翼,仿佛怕惊扰了一场美梦,“明昭……竟能再次得见仙颜?”
神女?明昭?
这两个词如同惊雷,在黛玉脑海中炸开。
明昭,当朝太子的名讳!他自称明昭,又称她为神女?难道这里不是她的梦,而是她的魂魄,不知为何,闯入了太子的梦境!
黛玉脸色煞白,怔忪不语,明昭眼中闪过一丝急切,但很快克制住,语气愈发温和,甚至带上了几分安抚的意味。
“上次混沌之中,得蒙神女于危难之际伸出援手,明昭方能挣脱无边苦海,觅得一线生机。此恩如同再造,明昭铭感五内,不敢或忘。只是当时意识昏聩,未能当面叩谢,深以为憾。”
黛玉见他言辞恳切,目光专注,仿佛她真是云端之上,悲悯垂怜的神祇,不由张了张嘴,想说自己并非神女,只是一个误入此地的孤魂,可话到嘴边,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这事实太过离奇,说出来,他会信吗?
“我……并非……”黛玉终是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声音微颤,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柔糯,在这寂静的水榭中格外清晰。
“神女不必多言,明昭明白,神女身份尊贵,非凡俗可知,能于此梦中再见,已是明昭莫大的福缘,不敢奢求更多。”
明昭何等敏锐,见她语焉不详,心下了然,必是有难言之隐,便不再追问,转而道:“此地简陋不堪,恐不及仙境之万一,却也难得清静。不知明昭可否冒昧,请神女稍坐片刻?”
太子的误会,将黛玉所有可能的辩解都堵了回去。
黛玉沉默片刻,没有再试图否认,她目光掠过水榭内的一几一榻,最终落在靠近门口的一张荷花凳上,缓缓走了过去,姿态虽带着戒备,却终究是坐下了。
明昭望着她,眼中波光涌动,难掩欢喜之情,险些失态,忙以拳抵唇轻咳一声,待神色恢复如常,方开口道:“敢问神女,明昭沉疴之时,所见无边黑暗与刺骨冰冷,可是堕入了某种厄难之境?”
黛玉闻言,想起第一次梦中,两人沉入冰冷的湖水,心有余悸。她斟酌着词语,轻声回道:“或许,是心魔所困,执念所缚。殿下能挣脱而出,便是心境澄明之兆。”
她不知具体缘由,只能依着佛理稍作点拨。
“心魔……执念……”明昭喃喃重复,眼底闪过一丝晦暗,随即又释然般轻叹,“神女所言甚是。若非神女牵引,明昭恐仍深陷其中,不得解脱。”他再次看向黛玉,目光灼灼,“神女此次降临,可是因明昭近日心境仍有滞碍,特来点化?”
黛玉被他问得心中一紧。她哪里有什么点化?她自己都迷茫无措。但看着他殷切的眼神,她只能勉强应道:“万物有缘,聚散无常。殿下既已醒来,便当珍重自身,不必执着于梦中幻影。”
明昭却摇了摇头,神情无比认真:“于神女或许是幻影,于明昭,却是真实不虚的救赎。”
他顿了顿,像是想到了什么,语气变得有些迟疑,“明昭醒来后,听闻荣国府一位林姑娘抄录经文时,诚心感动上苍,方引得神女垂怜,敢问神女,与林姑娘可有所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