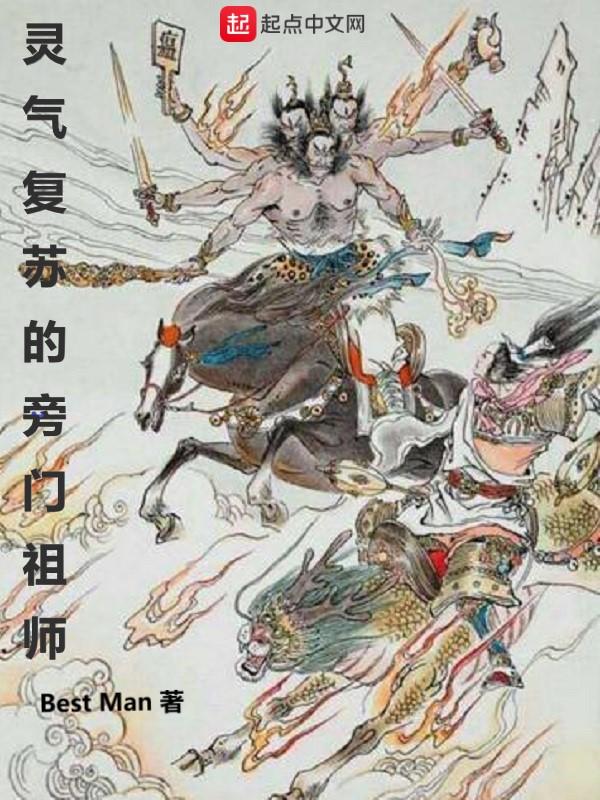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饮鸩止渴! > 十三 柳银簪(第2页)
十三 柳银簪(第2页)
蓦地,他抬起手来轻轻地揩去我眼角的泪水,是我许久未感受了的温度。
我又一次抬眸,这次却没再躲闪,而是咬牙将他眼中的星星点点的闪烁一览无余了。做完这个动作,我只觉得脑海中一片空白。
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忽然又凑进一步,我就这样毫无防备的被他吻上了唇。
在我梦境中出现过两次的场景,就这样真的发生了。我贪婪的享受着,如坠云端,全身都软绵绵的。
我被他缓缓松开,眼泪却依旧是汹涌澎湃的。
“阿鹿……”美好场景转瞬即逝这样的事于我而言已是家常便饭了。正因如此,我在面对反常的幸福时难免觉得不太真实,在珍惜之余还有点恐惧,怕一会梦醒了,我会更加难以接受。
然而,眼前人的温柔依旧的脸,他抚我脸时小心翼翼的手掌,方才他吻我时从未有过的美妙感觉……这一切不是真的又能是什么?
“采采,你不必担心,”他似乎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一字一句道,“明日我就请人带着聘礼到师娘那里说媒去。”我有些惊愕,欢喜之余还是无穷的担心,就连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在担心什么。
“可是,可是我对不起胡大哥……”我支支吾吾地道。他略微思索了一番,认真道:“你大可以不必为难。若实在是于心有愧,我可以等。都等了十年了,咱们再等上三五年再成亲又何妨?倘若到时你已觅得良人,我也绝无怨言……”
这一番情真意切的话,听得我心头直发颤。他顿了顿,像是犹豫了一番,又接口说道:“你当真看不出来吗?胡大哥他根本不喜欢你。他要同你成亲,不过是觉得到了该成亲的时候了。”
其实这个不用他说,我早在胡大哥嘴上说要娶我却迟迟未作出进一步行动时就猜到了。可是我难道就喜欢人家了吗?更何况我又临时改变了主意,不论怎么说都是对不住人家。不过既然阿鹿提到了这事……
我清清嗓子,反呛他了一口:“你既知道胡大哥不喜欢我,又为何执意要我嫁给他?”阿鹿果然面露难色,过了好一会儿才讪讪地开口:“因为他待你够好,而且……我本来以为你喜欢他。”
我有些惊讶,似乎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
阿鹿已经说要我嫁给他了,我却仍在迟疑,除了确实对不住胡大哥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与他现在身份相差悬殊,又十年未见,早已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了。然而这也可算作小问题。他既不甚在乎,我自然可以克服的。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他对我的爱是假的,是我精心设计出来的。
少年时的我,习惯了总是为所欲为,习惯了做什么都不计后果。
可无论如何,现在的我必须承担曾经种下的恶果。十年前满怀期待地在蘑菇汤里施下水长东之毒时,我一心只想着让阿鹿能像我喜欢他一般喜欢着我。可后来重重遭遇,我当时又岂能预料到?
本来盼着此生与他再无瓜葛,却终究缘分未了。重逢时他与我二人互作不识,我还道他真的将从前恩爱尽皆忘了--若真是那样,其实又有何不好?然而今日看来,他不仅没忘了我,反而十年来依旧是痴心不改。
一种熟悉的不安从胸膛缓缓升起了。我小时候背着阿娘吃多了粽子时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知道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感觉名为愧疚。现在我最对不起的人不是胡大哥,而是阿鹿。不管我答应他与否,此局都为无解之局。
水长东啊,我倒希望你的毒效能够小一点。我已误了一人青春,该当何解?
如若不是我暗中下毒,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只为一己私欲,阿鹿本可以寻得一个花容月貌又极负才情的名门闺秀。又何苦耽搁如此之久的宝贵年华,只为一个我?
我胸中满腔苦涩,却不是为别人,而是为我自己一时糊涂犯下的罪孽如今已再难赎清了。
我这人,实在是不够坦荡。他不认我时,我怨他冷心冷血。现下他明明已说了要娶我为妻,我却又犹疑不决,还添了一堆理由来拒绝他。
我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曾经做事雷厉风行,想一出便是一出的那个小姑娘,几时变得这般拖泥带水了?
我迟迟不回答,阿鹿的眼中便添了几分焦急。我清楚的看到,他的一张脸,连同右眉眉尾处的那颗小痣,都在轻轻地颤抖,像雨天被浇坏翅膀的鸟儿。
阿鹿,我该怎么做?若我不答应你,你必定肝肠寸断,相思成疾。可我若应了你,却要我日后怎么做?难道你真能凭那一剂毒药,便死心塌地爱我一辈子么?
罢了,反正是我自己造下的孽……
“好啊。”我挤出一个久违的微笑,眼中却仍是泪光莹莹的。
阿鹿方才还有些不安的面孔上登时呈现出喜色,笑道:“那你说,你我何时成亲才好?”
我略微思索了一番,太近了肯定不行,那也太辱没胡大哥了。可若真的等个三五年,太迟了又恐再生变故。
“那便五月廿九好了。”说罢,我意味深长地望向他。他惊了一下,立即会意了:“是……你将我从山脚下救起的那日?”
我笑而不语,心想:你果然全都记得。
“劈里啪啦--”循声望去,果然是胡大哥的鞭炮声。这要是搁在幼时,我必定要跑出去凑一番热闹的。然而时光荏苒,我似乎已好久不喜热闹了。
虽说不喜热闹,但我也厌恶孤寂。好在此时此刻我根本不孤寂,而是有一个在我心中十全十美的身边人。身边人用他温热的掌心轻柔地摩挲着我的脸庞,那月色般的目光也片刻不离地凝视着我。
我想到过时间一旦拖下去就要发生变故,却没想到这变故这么快就来了。
从欢声笑语的黑夜中,遥遥地走过来一个人。我还道他也要去放鞭炮,不料他丝毫没在热闹的人群中停留--竟是径直走入了闻琴阁内。
我这才看清了他的脸:眉毛高高的,隔了好远才是一双细长的眼睛,鼻子又粗又长,模样是说不上来的怪,看上去大约四十来岁的样子。大过年的他从头到脚穿了一身黑,更是有些诡异。
我迎上去笑道:“客官,您来的不巧了,从今日到初五是我们的封箱日,要不您……”还没等我说完,他就冷冷地打断了我:“姑娘误会了,我今日前来一不为饮茶,二不为住店。”我疑惑道:“那您是来干嘛的?”
他十分别扭地笑了笑,笑得我汗毛直立:“我是来找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