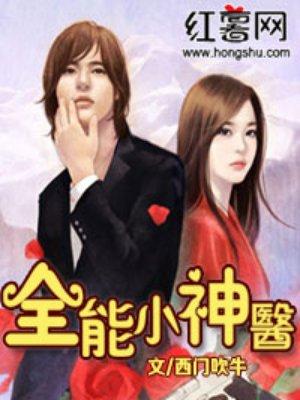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饮鸩止渴! > 番外二 前尘难忘font colorred番外font(第2页)
番外二 前尘难忘font colorred番外font(第2页)
好在我生性活泼,时不时地说些漂亮话,至少让她稍微轻松一点。
她在族中的名声越来越不好了。因为她一再推脱,不嫁有婚约之人,反倒与一个男徒弟接触甚密。
可他们都误会了。我和师父虽然日日独处,但每天口中交谈的真的只有毒术而已。
我以为六年时间已经够长了,可我忘了,我们两人之间的距离比之还要遥远。
八年究竟是多长?我不知,也不敢想。
短短八年时间,竟隔绝了我此生所有的爱恨嗔痴。
那家人又来找过她了,她拒绝无果,只好又用了一些拙劣的理由搪塞过去了。回到我们约定制毒的老榆树下时,她苦着脸一句话也没说。
我也无甚话可说,只好低下头去不看她。
可我到底是开口了,声音哑哑的:“师父,你这辈子要活得长一点。”
“人生苦短,我活那么久做什么?”
“你要比我多活八年。这样咱们便能一同投胎了。到了下辈子,咱们也许能一同长大了。”
我无意间的一句话,很快被师父捕风捉影到一点苗头。
她定定盯住我,眼中焕发出久违的炽热的光芒。
“一同长大,做什么呢?现在不是照样能相互作伴么?”
“来世倘若你我一同出生,便犯不着再做这师徒了。”我喉咙里的声音已经细不可闻。
“犯不着做师徒,那又能做什么呢?”
我的喉咙彻底被堵住了,简简单单的再寻常不过的两个字,硬是连音也发不出。
最后,我说出的是这一句:“弟子糊涂了,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终究纸是不能包住火的。这般日子,纵使问心无愧,也必定煎熬备至。更何况,我心里的愧已经快水漫金山了。
小时候的傲气渐渐淡了,我更多时候觉得无论山水,皆是混沌的一片,如同镜花水月。
我遇见师父那日,曾被我视作再平凡不过的一日。
这一日也是。
我采了一朵绚烂夺目的赤灼花,兴高采烈带了回去。因为我心中想着:师父戴上它一定好看。
但其实我比谁都清楚,师父不喜欢簪花,更不喜欢艳俗的大红色。我只是找了一个借口,想早点见到她。
也幸亏我早早回来了。
因为在大榆树下,我隔着好远就见到了一个男人,他不仅长着令人作呕的肥头大耳,还做着更加令人火冒三丈的动作:他正在撕扯我师父的衣裳。
我只觉得一股怒火往脑门上冲,一时间什么也顾不得了。
我把那人打得鼻青脸肿,血流不止。直到有一双手轻柔地拉住我,我才愣了一下,不得不做罢。
狼狈逃走时,那人嘴里还不停骂着:“这个贱人,老子早就知道你跟你细皮嫩肉的小徒弟有一腿了!你们给老子等着……”
可我没再去管他了,因为我的全部心思一时之间都给了那双停留在我手腕上的手。那双冰冷的、柔软的手。
知她衣衫不整,我根本不敢回头,只好这般背对着她,也正好不让她看见眼中涌出的泪。
“师父,我……”
方才还血气方刚的我,瞬间变成了一只受惊的兔子。
“你给他打坏了不要紧,他给你打坏了可怎么办呢?”这声音如春露秋水,在我心间荡漾开来。
我任由她拽着我的手腕离开,又任由她在我受伤之处温柔地涂抹冰凉的药物,所到之处惊起一片涟漪。
可在这过程中,我始终不敢抬起头来,再好好看她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