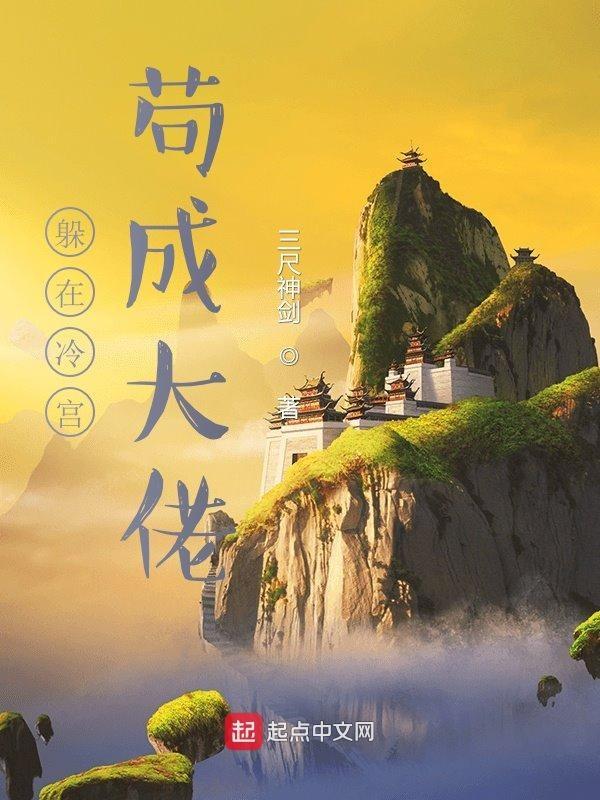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墨染时光梦笔寒 > 昏迷(第2页)
昏迷(第2页)
她开始不受控制地回想事发时的每一个细节——那声来自慕容墨染的、撕心裂肺的警告,那声来自头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破空声,以及……花盆坠落前,她似乎无意中瞥见的,三楼阳台那个一闪而过的、模糊身影。
她的心脏猛地一缩,一股寒意瞬间窜遍全身。
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极其缓慢地,转向了坐在对面的慕容烬歌。
慕容烬歌似乎感应到她的注视,身体几不可查地一僵,随即抬起头,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带着关切和困惑的表情:“姐,你怎么了?姐夫他……他一定会没事的……”
慕容青瓷没有回答。她的目光与弟弟对视了一秒,仅仅一秒,她就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移开了视线。那眼神里的东西太复杂,有怀疑,有恐惧,有不愿相信的挣扎,更有一种洞悉真相后的、冰冷的绝望。她不敢再看下去,她怕自己会当场失控。
她猛地站起身,声音因为极力压抑而显得有些沙哑和怪异:“我……我回去给时默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医院里说不定要用。”这个理由合情合理,甚至显得有些体贴。
慕容衿雪想说什么,但看到她失魂落魄的样子,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姐,你小心点。”
慕容青瓷几乎是逃离了休息区,快步走出医院,拦了一辆出租车,报出别墅地址。一路上,她紧咬着下唇,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身体因为某种可怕的猜想而微微发抖。
回到空荡荡、仿佛还残留着生日派对虚假温馨的别墅,她没有丝毫停留,径直冲上三楼阳台。
夜晚的寒风扑面而来。她的目光第一时间就锁定了阳台边缘——那个原本摆放着沉重陶盆的位置,此刻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清晰的、积着些许灰尘的圆形印记,像一个无声的指控。
一瞬间,所有的怀疑都被证实了。
慕容青瓷双腿一软,几乎要瘫倒在地。她扶住冰冷的栏杆,才勉强站稳。巨大的愤怒、悲伤、恐惧,如同海啸般几乎将她吞噬。她几乎要尖叫出来,想要立刻冲回医院,揪住慕容烬歌问个明白!
但下一秒,一个更强烈的念头占据了上风——保护!保护这个家,保护…对,如果文时默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还会要自己吗?
她不能乱!她必须冷静!
她深吸几口冰冷的空气,强行压下翻涌的情绪,眼神变得决绝而冰冷。她迅速转身回到屋内,找来一条干净的湿毛巾,重新返回阳台。
她开始擦拭。极其仔细地、用力地擦拭着那个圆形印记,不放过任何一点泥土痕迹。接着,她像是发了疯一样,将旁边其他花盆也全部搬开,将下面可能留下的、任何可能与慕容烬歌有关的脚印、或者其他痕迹,统统擦拭干净。她做得那么专注,那么用力,仿佛要将这场罪恶连同痕迹一起,从世界上彻底抹去。
做完这一切,她站在阳台中央,环视四周,确认看不出任何异常后,才快步回到书房,打开了连接阳台监控的电脑。
屏幕上,监控软件界面清晰可见。她握着鼠标的手在颤抖,光标在那个记录着事发时刻的视频文件上停留了许久。
最终,她却没有点开。
因为她已经不需要看了。这场“意外”究竟如何发生,她心知肚明。
下一刻,她做出了一个更决绝的决定。她笨拙地关闭电脑,拔掉电源,然后找来螺丝刀,生平第一次,有些粗暴地拆开了电脑主机箱。她辨认出那块存储着监控视频的硬盘,用力将其拔了下来。
她回到卧室,快速收拾了几件文时默的贴身衣物,然后将那条擦拭过痕迹的毛巾和那块冰冷的硬盘一起,塞进了袋子里。
走出别墅,夜风更冷了。她拦下出租车,在回医院的路上,恰好看到一辆正在作业的垃圾运输车。她立刻让司机停车,快步走上前,毫不犹豫地将那个装着毛巾和硬盘的袋子,扔进了正在压缩垃圾的巨口中。
看着那袋承载着可怕秘密的东西被机械无情地吞噬、碾碎,她仿佛才松了一口气,但心头那块巨石,却更加沉重了。
当她再次回到医院休息区时,脸上已经看不出太多的波澜,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一种背负了巨大秘密的、异样的平静。她将带来的衣服放在一边,重新坐下,沉默地加入了等待的队伍。
只是这一次,她的等待里,除了对丈夫生命的担忧,更多了一层对家庭未来分崩离析的、更深沉的恐惧。她知道,有些东西,从那个花盆落下开始,就已经彻底改变了。而她,选择成为了这场罪恶的沉默共谋。
医院顶层,ICU病房。
空气里只有医疗仪器规律而冰冷的滴答声。文时默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色苍白如纸,鼻息微弱但平稳。各种管线连接在他身上,像一道道脆弱的生命线。
文母牵着文景晨的手,几乎是踮着脚、屏着呼吸走到病床前。七岁的文景晨已经懵懂地知晓了“生病”和“危险”的含义,他看着平日里高大温和的爸爸此刻毫无生气地躺在这里,大眼睛里迅速蓄满了泪水。
“爸爸……”他带着哭腔,小声地喊了一句,见爸爸没有反应,终于忍不住,挣脱奶奶的手,扑到病床边缘,小手小心翼翼地、带着颤抖,轻轻抚摸上文时默没有血色的脸颊,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爸爸,你醒醒……晨晨害怕……”
孩子稚嫩而悲伤的呼唤,像针一样扎在在场每个人的心上。文母的眼泪再次决堤,她捂住嘴,生怕自己哭出声来,另一只手轻轻放在孙子的背上,无声地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