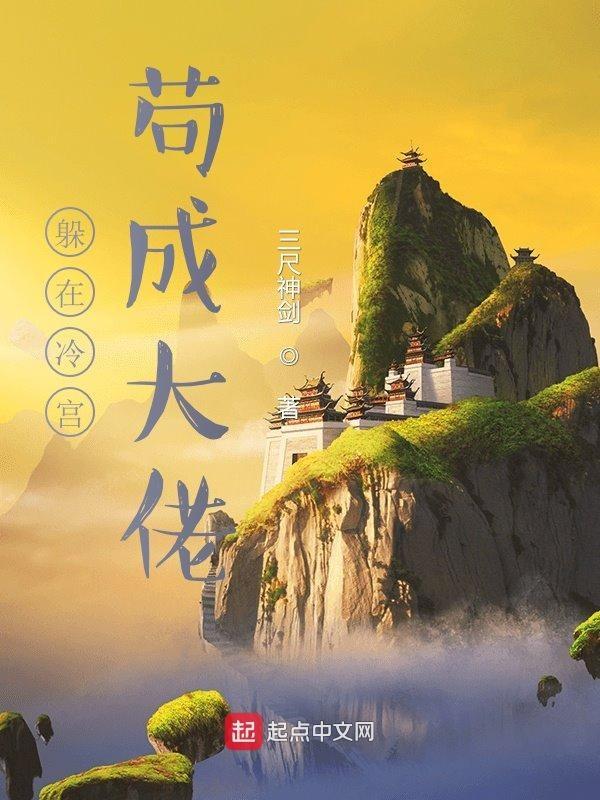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综英美剑客 > 第295章(第1页)
第295章(第1页)
薇洛就扮了个鬼脸,“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
但她就算抽条拔高了不少,发顶也只堪堪够到埃利奥的胸口。埃利奥低头瞧着她,微微地笑了一笑。六道骸也没忍住笑了一下,但蓝的红的灯光到处乱闪,已经捉着朋友的手跑开的薇洛自然没瞧见他们的神情,只是遥遥地冲他们挥了挥手。很快,她们就像几条自由的小鱼那样,活泼地游进了人群里。
“走吧,”六道骸招呼埃利奥,“我们去和吉安娜打个招呼,然后就可以撤了。”
埃利奥纳闷地跟上,“我还以为你会喜欢派对。”
“我只喜欢死人的派对,”六道骸阴暗地回答,“这种吵得要死的……”他没把话说完,前面就有侍者端着银盘恭恭敬敬地走了过来。六道骸于是随便挑了杯甜滋滋的白葡萄酒,捏在戴着皮手套的手指里,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句埃利奥,“你想喝点什么?”
“香槟。”埃利奥告诉他。
六道骸于是替他拿了杯香槟。埃利奥接到手里,不由得多看了那侍者两眼;他并没有别的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全程微微低着头,避开了和六道骸的任何眼神接触,脖子僵硬得像是卡在肩膀之间的水泥柱似的。
他不敢看六道骸的眼睛。埃利奥想。
“你看他干什么?”六道骸就像后脑勺长了眼睛似的问。
“随便看看。”埃利奥就说。
六道骸笑吟吟地看了刺客两眼。埃利奥也看了看他,手腕轻轻一转,用香槟碰了碰六道骸手里的白葡萄酒。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红毯边上站定了。一路畅通无阻,吉安娜领着她的保镖队伍正从石头拱门里走出来;那拱门里两千年多前也是这样走出角斗士,放出野兽的,只不过吉安娜的衣着比他们都要体面一些,雪一样白的毛领外套裹着银光闪闪的鱼尾裙。也像两千多年前那样,宾客们响起一阵欢呼的潮响,音乐一时震耳欲聋,差点让埃利奥没听清六道骸说的话。
但埃利奥还是看清了那句话,六道骸是这么问的,“干什么?”
“庆祝一下,”埃利奥说,“不行吗?”
“为了吉安娜?”六道骸挑眉。
“为了桑蒂诺的死。”
六道骸笑了。他从善如流地碰了碰埃利奥的酒杯,“为了你得偿所愿。”
“也为了彭格列。”埃利奥和他碰杯。
他们相视一笑。吉安娜正巧在这时走到他们面前,含笑问候,“看来派对还算让你们满意。”
六道骸适时摆出一张风度翩翩的完美假笑脸,“很满意。”
他们寒暄了一阵,六道骸再次恭贺吉安娜得偿所愿,显然懒得再想别的祝酒词;吉安娜莞尔,同样祝愿彭格列繁荣昌盛,又祝愿埃利奥,“愿好运常伴您的刀刃!”
埃利奥私底下觉得她看起来有点像一只正优雅地按着爪子的雪豹,又或者别的什么。吉安娜的耳环冰柱似的垂下来,闪着柔软银亮的光,晃了一下埃利奥没戴着墨镜的绿眼睛。她最后冲六道骸和埃利奥微微一笑,步态平稳地往前去了,继续和其他来宾寒暄。
“你喜欢她的耳环?”六道骸奇怪地问。
埃利奥刚把那杯香槟喝完,正重新戴上他的墨镜,“它让我想起一个朋友。”
六道骸不轻不重地“哦”了一声,没再问下去。他们像模像样地又在原地逗留了一会儿,六道骸为埃利奥介绍了几张熟面孔,接着就默契地溜之大吉,消失在人山人海之中。
“我先撤了,”六道骸告诉他,“赶着回去打刺客信条。”
埃利奥没忍住多问了一句,“真的?”
六道骸就冲他粲然一笑,“假的。”
埃利奥哑然失笑。他最后对已经撤出几人远的六道骸挥了挥手,后者也远远地对他点了一点头;那披着风衣的高个身影很快被舞动的人群遮挡得无影无踪,埃利奥也转过身,想方设法地拨过人群,往上走去了。在几千年前,刺客现在踩过的这些台阶是斗兽场的观众席,埃利奥一边拾阶而上,一边听到地面上欢呼沸腾的派对人声,不由得有点儿身临其境的恍惚感。
“这和古罗马的斗兽表演又有什么区别呢?”
墩柱后面,有个熟悉的冷淡声音轻飘飘地说出了埃利奥心里正想着的事情。埃利奥为这巧合短暂地愣了一下,正打算走上前去打个招呼,恰好又听到另一个相伴数年的嗓音。那说话声仍然和他们上次见面时别无二致,平和有如潺潺流水,“也许是野兽死在了斗兽之前?”
埃利奥的脚步彻底顿住了。他在原地默默地停留了一会儿,最后还是通过鹰眼看到那两位结伴而行的圣殿骑士正慢悠悠地前行,眼看着就要走出墩柱背后的阴影瞧见他了,刺客这才闪身躲进了黑暗里。
“你不认为是斗角士先死了吗?”加拉哈德用状似好奇的语气问。
“但我们从不和野兽合作,不是吗?”雷欧波德反问。
这回轮到加拉哈德失笑了。但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慢慢地,自然地停了下来,往下望去。埃利奥也往下看了看,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三千多人正挤在那个据说足以容纳五万多人的竞技场里狂欢舞动,歌手照旧唱着歌,灯光照旧闪着灯。
他没有说话,雷欧波德也没有再开口。他们只是站在这里,俯瞰了一会儿,就像两个寻常的游客似的。然后,没出一声地,加拉哈德不紧不慢地对雷欧波德点了点头,甚至没看雷欧波德的回礼,就自顾自地拾阶而下,漫步离开了。
现在,这儿只剩埃利奥和雷欧波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