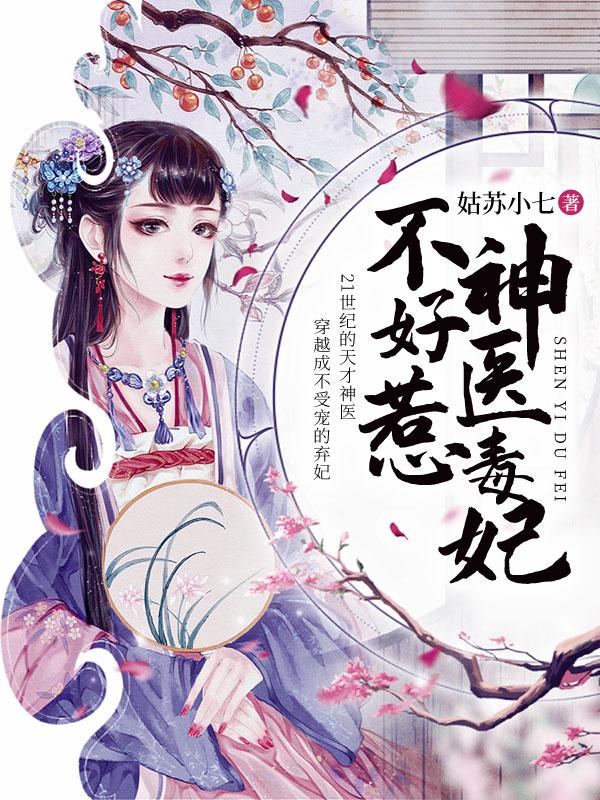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银色铁轨TXT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相较之下,李子桐是个更合适的倾诉对象。虽然话少,但不会反驳,也不会表现出不耐烦,始终坐在后排的座位上静静聆听。
“我父母就是两个不怎么喜欢对方的人,但凑巧被婚姻关系束缚在了一起,因此矛盾永无止息。他们从不自己找原因,总习惯于把责任归结在我身上,数不清多少次了,母亲当着父亲的面对我说,如果不是我,她早就和父亲离婚了,这场婚姻就是一个错误。那我算什么?“错误”平方后的累积结果?父母常常会不经意地把孩子推向自我厌恶的深渊。”
“唔,你也挺不容易的啊。”李子桐少见地安慰道。
偶尔聊天的话题也会偏离到李子桐的家庭情况上。
她有个弟弟,这是相当少见的。那时超生的处罚非常重,不光是罚款,国营单位的家长还有可能丢工作。身边的同学除了她以外都是独生子女。
我问她有个弟弟是什么感觉。她说没有什么特殊的。
“父母对我们相当公平。”
“是吗,相当羡慕你家的环境呢,你父母堪称养育子女的模范,真想让他们给我家那两位上上课。”
她似乎想再说些什么,但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公交车到站了。我意犹未尽地结束话题,在路口与李子桐分道扬镳。
很多年后我忽然意识到,那段路上的经历宛若自己的人生。一个人活着时,道路笔直向前,望不见尽头。而若有人同路相伴,总转眼间就到达分岔路口。
不过若是被问起我们那时关系如何,我还是觉得连普通朋友也算不上,只是认识的人而已。
在学校里,我与李子桐同一个班级。两人自然会不时地遇上,或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或在进出教室时偶然相遇。然而她似乎对我的存在毫无兴趣。即便我作为课代表向她收作业,她也不会稍微动动眉毛,更不会将视线从作业本上移开。那双瞳仁毫无变化,依旧缺乏深邃感和光芒。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她的做法。那个年龄的孩子很喜欢拿要好的男女开心起哄。不过她做得未免也太绝情了。
她似乎格外不想成为瞩目的对象,在班级里总保持着孤立,和谁都不说话。课堂上偶尔被教师点名时,她的回答总是言简意赅(有时干脆说自己答不上来)。考试分数也很不稳定,她偶尔会考出全班第一的成绩,但下一次一定会滑落至第十名上下的位置。我总觉得她是故意的。说不定是为了避免成为全班的焦点人物,才在答题时精准控制分数,这可比单纯拿第一名还难上不少。
不过看店的时候例外,面对租借碟片的客人,她通常表现得很有礼貌,有问必答,甚至会主动推荐热门的电影。一次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来了个秃顶的中年大叔。李子桐主动向他打招呼,介绍了最新的进货情况。
“看不出来,挺会做生意的嘛。”客人走后,我感叹道。
“那人是熟客。”她耸耸肩,“不好好接待的话,父母会发脾气的。”
我回想起自己前几次来借录像带时,被她各种嫌弃的经历,不由得感觉到了差别待遇,“我最初来的时候,你的态度格外差劲呢。”
“谁叫你选了那种碟片。我讨厌恶心的人。”她直言不讳地回答。
拜托,那些所谓的恶心碟片可是你家音像店贩卖的哎,而且阁楼上还有更直接更露骨的。不过这话我没说出口,一来明白那是人家的生计需要,市里所有的音像店几乎都卖那种录像带;二来她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大概是真心厌恶这类话题吧。
“那时我是被迫过来借的。”我抗议道。
“我知道,后来不还帮你的吗……不要再谈这种事了。”她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电影上。
没等我看完音像店的录像带,店主已开始换上碟片。小学最后的一年很快过去了,我依旧没摆脱对世界末日的担忧。但学还是要上的,我背熟了荀子的“劝学”,学会了立体图形表面积和体积计算,考出了一个勉强拿得出手的升学考试分数。
毕业后,我和她进了不同的初中。青春期,一个非常微妙的年龄段。同学变了,校服变了,课本变了。自己的体形、声音以及对世界的认知也开始急剧变化。
初二时有一部港台偶像剧全国热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以现在的眼光,恐怕想象不出这种俗气的偶像剧到底有什么值得在意之处。可那时的媒体纷纷把矛头指向了剧里的恋爱问题,价值观问题,以及片中四个男主角不阴不阳的长发造型。认为会对年轻人造成相当不良的影响。
而恰逢此时,本市发生了一起高中生怀孕后自杀的事件。教育局十分重视,相关文件也下达到了我们的初中。班主任开始排查起班里早恋的学生。事实上,真有那么两三对。
这事班里的学生都心知肚明,但家长层面完全不知道。他们相当惊讶,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听闻此事的母亲也担心起来,不但禁止我看任何偶像剧,还再三盘查我的朋友关系,强调学业为重。
我嘴上唯唯诺诺,心底不以为然。母亲完全是想多了。对自己的儿子,不知道她哪来的充足自信。
班里谈恋爱的男生,基本都有些共同特征,尽是些能说会道且相貌俊朗之辈。这两个条件我都不够格:朋友不多,和女同学更是没有共同话题;相貌平平,个子矮,座位位于前三排(我比同龄人发育晚些,高中才开始蹿个子)。
不过学习考试之余,我有时也忍不住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数遍身边,能说得上话的异性也只有李子桐了,虽然她的性格奇怪了些,但外貌方面条件过硬。属于只要不开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