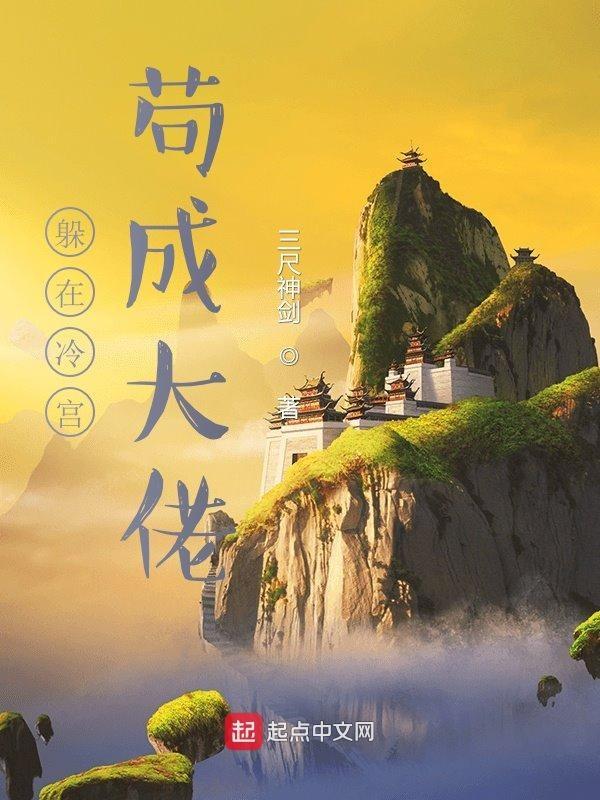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铁轨颜色 > 第80章(第1页)
第80章(第1页)
车起步后,我为父亲的误会向李子桐道歉。
“我一点也不介意啊,挺有意思的。”她笑着说。
“可你为什么阻拦我向他透露真名呢?”我忍不住问。经过媒体这么一传播,著名导演李子桐的事迹早已人尽皆知了,完全没有掩饰的必要。
“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就那么做了。”她吐了吐舌头,“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怕他吧?”
“怕我爸?”我奇道。
李子桐郑重其事地点点头,“高中时因为案件的事,我去过审讯室好几次,他当时也在。”
“哦……”我想说句玩笑话化解尴尬,“那也不用怕到现在吧,他早就退休了,现在不过是一个到处下棋喝茶的平常老头而已。”
她怔了怔,“
退休了?可两年前他还找到影视公司,想让我配合调查呢。”
“哎,那他见到你了?”
“没,当时我出国了,回国很久后才听说的。”
两年前——我感觉相当不对劲。八年前,父亲就因工伤办理内退了,怎么还要查案,还盯着李子桐不放?而且据我所知,他也不是“录像带”案件的直接负责人。
“怎么了?”看出我脸色的不对,李子桐问道。
我装出笑容,摇摇头,“没事。”
可能我的演技在大导演的眼里并不过关吧。之后我们在车里谁也没说话。出租车安静地开往市郊的殡仪馆。
我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葬礼。
来的人挺多,挤在殡仪馆的灵堂小厅里略显局促。厅里的啜泣声不绝于耳,但仔细一看,大伙的眼里甚至都没有些许悲戚之意,眼眶干得有如沙漠。少数几人眼眶红了,每当谈起死者,他们就条件反射式地用指背狠狠刮擦眼角,抹去并不存在的泪珠。
李子桐一走进小厅,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她的身上。不少人当即围拢过来,有的嘘寒问暖,有的加倍傲慢,以长辈的身份对她的姗姗来迟指手画脚,更有甚者直接问起她打算如何料理李家的遗产。李子桐含糊应答,不想理会的就直接装作没听见。而我则尽力扮演护花使者的角色。
说话间,一个中年大叔向我们挤过来,他双眼略为突出,仿佛脑压过高,让他呈现出瞠目而视的表情。头发稀疏,体格却仍显粗壮。长满了黑色体毛的手腕上,套着一条拇指粗细的金链子。他一走过,周围的人就像被风暴刮弯的树枝一样纷纷侧身。
“那就是我二叔,叫李开毅。我不想见他。”
“那怎么办,有作战计划吗?”
“有,我去趟洗手间。”
李子桐转身就走。李开毅想追,但我没让路,人又多,他只得瞪了我一眼离开了。
见她安全离开,我长舒一口气,挤出人群,找了个安逸的角落靠着。
灵堂中央摆着朴素的棺材,摆了几篮可循环利用的白菊花。棺木看上去十分单薄,仅仅比装橘子的木箱子结实点。棺材盖没开,恐怕是由于遗体发现时的糟糕状态,即使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再努力,也难以修复到不骇人的地步。现场标识死者身份的只有棺木后的灵位和遗照。
那张遗照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黑白色的遗照本身就相当不吉,这张相片里的人脸又十分模糊,像是笼罩在薄雾轻纱里一样,更显得鬼气森森。
没等我凝神细思,已听到身后有人讨论起来,“你说李家这个小丫头怎么搞的,遗照选了这么个不清不楚的。”
“就是,”另一个女声在一旁帮腔,“自己弟弟的葬礼还迟到,简直是应付了事的态度。”
“你们没听说吗,李天赐根本不是她的亲弟弟,所以才这么胡搞。”
回过头一看,是三四个膀圆腰粗的中年妇女,围成一圈说得吐沫星子横飞。
“而且她连李天赐的照片都找不到,一张都没有。最后只能从身份证照片上拓印。根本一点感情都没有。”
原来如此,是从小尺寸的照片放大导致的像素过低。仔细一看,脸的边缘明显带着锯齿状。但即使搞明白了相片模糊的原因,那张脸仍让我感觉十分不对劲。
稍倾,工作人员进场,正式的葬礼仪式开始。没什么可说的,老一套的流程,每每如此。遗体告别,火化,下葬。
众人排队烧完纸钱后,仪式算是画下了休止符。从墓地出来,早有订好的大巴车等在路口,接大家去吃午饭。李子桐拉了拉我的袖子,我知道她不想去。由于葬礼的肃穆氛围,刚才谁也没多说题外话,但接下来就不一定了。很多人一脸憋了很多话想说的样子,等下宴席上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若是有人白酒灌多了,演变成鸿门宴也说不定。
李子桐借口身体不适,推脱着不想去。但众人不依不饶,一边嘴里说着客套话,一边把她往大巴上拉。我奋力帮忙,但势单力薄。此时那个叫李开毅的二叔居然出手相助,他嚷嚷着“人家远道而来不容易”,几乎是靠蛮力把李子桐从人群里硬拉出来。
路旁还停了一辆丰田花冠小轿车。李开毅护着我们坐进后座,自己发动汽车迅速逃离现场。
“子桐他们累了,我们先送她回家吧。”李开毅对着副驾驶座说,我这才注意到那里默不作声地坐着一位中年女子。
“好啊,你开慢点,注意安全。”女子身穿灰色毛衣,胖乎乎的,转过头来对李子桐和蔼地笑了笑,“你也是不容易啊,后座有靠枕,你斜倚着休息一会吧。”
李子桐冷漠地说了句“谢谢”,闭上眼睛没再开口。似乎也明白他们没安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