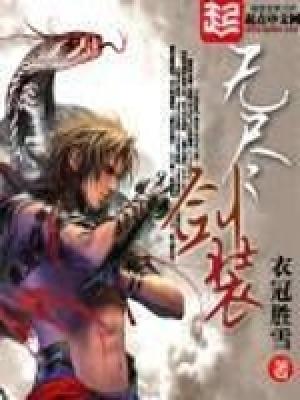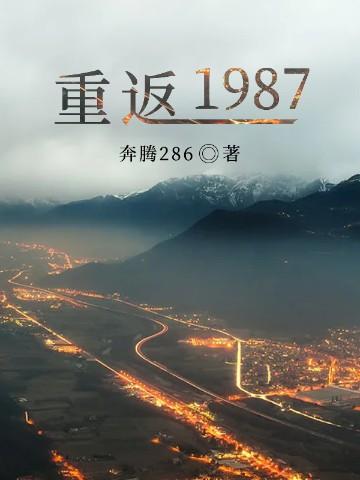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魏晋不服周笔趣阁免费阅读 > 第207章 事出反常必有妖(第2页)
第207章 事出反常必有妖(第2页)
随即命人敲响薪火台铜钟??三长两短,全境警讯。这是火种队最高指令,意味着“核心传承面临灭绝威胁”。按照约定,敦煌发出信号后,所有微学堂必须在十二个时辰内完成三件事:转移典籍副本、启动地下讲学网络、向邻近盟友通报危机。
与此同时,她亲自修书七封,分别送往于阗、鄯善、吐谷浑、高昌、伊吾、凉州义士团,以及建康那位御史台主簿。每一封信中都附有一枚从莎车带回的焦木碎片,并写着同一句话:“火可焚屋,不可焚心。今贼刃加颈,吾辈更当发声。请速联署《护法共誓书》,以民意压邪谋。”
启明问道:“你要发动万人联署?”
“不止万人。”阿禾冷笑,“我要让每一个识字的人,都知道王允之杀了谁。我要把他的名字和那两具悬首示众的尸体一起,钉在《民问录》最醒目的位置。”
计划迅速展开。敦煌城进入战时状态。白天,讲坛照常开讲,内容全部公开备案,滴水不漏,令监讲官挑不出半点错处;夜晚,则有数十支秘密队伍穿梭街巷,将《岁问精华录》缩印成手掌大小的薄纸卷,藏于粮袋、鞋底、发簪之中,送往周边绿洲。更有巧匠制作“盲文陶片”,供视障者触摸学习;乐师将重要法条编成十二曲《律令谣》,通过商旅传唱四方。
七日后,第一份《护法共誓书》由高昌送来??三百七十二人联名,包括僧侣、商人、工匠、农妇,甚至两名投降的匈奴老兵。他们按下手印,誓言:“宁舍性命,不弃问答桩。”
紧接着,于阗送来五百零八人签名,附带一份血书:“法若死,我等亦死。”
吐谷浑部落则以十二面铜鼓为证,每面鼓上刻一人姓名,象征“鼓声不息,律脉不断”。
最令人震动的是建康方面的回应。那位御史台主簿竟联合三十一名低阶官员,在朝会散后集体跪奏天子,呈上《救律十二条陈》,痛陈王允之勾结地方酷吏、打压民间申冤之路的种种罪行,并请求彻查焉耆兵变幕后黑手。奏章末尾写道:“昔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今阿禾女士立《民问录》而奸佞侧目。若以言治罪,是自绝于天下人心。”
天子震怒,下令暂停太常寺对敦煌讲坛的监督权限,另派钦差大臣赴西域调查实情。
消息传到敦煌那夜,全城点燃油灯。百姓自发走上街头,每人手持一盏,组成巨大的“问”字,映照戈壁如白昼。孩子们围着薪火台跳舞,唱的是新编的《律娘子歌》:“驼铃响,黄沙扬,阿禾老师教我讲;官欺我,我不慌,掏出律条大声嚷。”
然而风暴并未停歇。九月初三,伊吾方向传来噩耗:乌仁娜病危。她在组织难民重建莎车微学堂时感染风寒,加之多年积劳,肺腑俱损。临终前,她留下遗言:“告诉阿禾,我没有完成的事,交给她了。草原上的孩子,一个都不能落下。”
阿禾闻讯当日未曾落泪,只是默默取出乌仁娜当年在雪原上写的血书残片,放入檀木匣中,与那首匿名诗并列。当晚,她在藏书室写下一篇祭文,不发讣告,不举哀仪,唯独要求各地学堂在同一时刻齐诵《启蒙章》第九条:“教育之权,属诸万民,无论男女、贵贱、胡汉、残健,皆得平等受教。”
次日清晨,她召集所有骨干,宣布一项前所未有的行动:“我们要办一场‘万里联讲’。”
“何谓联讲?”
“自敦煌始,经高昌、龟兹、疏勒、于阗,直至建康太学门前,连续三十三日,每日一城,同步开讲同一主题??《人民为何需要法律》。全程由商队接力传递讲稿,沿途百姓可自行加入,形成流动的讲坛长龙。”
“若是官府阻拦呢?”
“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民心不可违。”
计划启动当日,恰逢霜降。第一讲在敦煌举行,主题为“起点”。阿禾站在薪火台上,面对万人听众,没有讲条文,只讲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焉耆某村,八岁女童阿依夏,因父亲早亡,族老欲将其许配六十老翁换聘礼。她记得曾在问答桩下听人念过《婚姻自由法》,便连夜逃出村庄,徒步四十里找到微学堂求助。教习依据律法介入,最终迫使族老退婚。如今,那女孩已在学堂读书半年,上个月还在作文中写道:“我想当一名律娘子,帮更多妹妹逃跑。”
话音落下,台下一片啜泣。许多母亲抱着女儿落泪,许多父亲低头沉思。
讲毕,驼队出发。第一卷讲稿密封于防水油布之内,由启明亲自护送,奔赴高昌。与此同时,敦煌开启第二讲,主题为“抗争”。一名曾被冤囚十年的老兵登台,讲述自己如何靠记忆中的《刑狱审查法》条款,在释放后成功申诉,追责三名贪官。
而在遥远的建康,那位御史台主簿正悄然联络太学诸生。当得知“万里联讲”即将抵达的消息后,他发动百余名青年学子,在太学讲坛外搭起露天席位,预备迎接敦煌来使,并公开宣读《民问录》最新篇章。
十一月中旬,联讲队伍进入凉州境内。此处本是王允之势力重镇,官府严禁集会讲法。然而当驼铃声传入武威城外,竟有数百百姓冲破封锁,携凳带席,在荒野中围出一片临时讲场。官兵赶来驱赶,带头人却举起手中的《人身保护令》抄本,高喊:“我们只是听人讲法,犯了哪一条律?”
士兵们迟疑了。带队校尉最终下令:“不准动手。这些人……手里都有文书。”
那一刻,法律不再是虚影,而是实实在在挡在弱者身前的盾牌。
十二月初八,联讲终至建康。启明率队走入太学广场时,已有三千余人等候。他们中有士族子弟,也有佃户仆役;有白发老儒,也有垂髫幼童。钦差大臣亦到场见证,默然坐在角落。
启明登上高台,打开密封讲稿,朗声宣读阿禾亲撰的终章??《火种不灭》:
“有人问我,为何执着于此?我说,因为我见过太多沉默的死亡。一个女人被夫家毒杀,只因她学会了算账;一个少年因揭发贪官,被投入枯井;一个村庄集体失语,因为没人敢问‘凭什么’。
法律不能复活死者,但它能让活着的人不再恐惧。
我们不是要推翻什么,而是要建立一种可能:在这个世上,弱者也能抬头说话,穷人也能主张权利,女子也能执笔释法。
这条路很长,或许我走不到尽头。但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接过这盏灯,黑暗就永远赢不了。”
全场肃立。良久,掌声如雷,久久不息。
数日后,天子再次下诏:正式承认“岁问”制度为国家辅助司法机制,授权各地设立民间律议所,受理民事纠纷;赦免所有因传播律法而获罪之人;追赠李元朗、乌仁娜等人“贞义学者”谥号,并命史官将其事迹录入《儒林传》。
圣旨送达敦煌那天,正值春分。第一缕阳光洒在薪火台上,照亮墙上新刻的一行大字:
“法之所在,即是故乡。”
阿禾站在关楼之上,望向东方。她知道,王允之仍未倒台,斗争仍在继续。但她也看见,南方某个小村的祠堂里,一个小女孩正用炭条在地上写字??
“我有权拒绝嫁给老头。”
风起时,万千柳絮飘向天际,像无数细小的追问,飞越山河,落入泥土,静待来年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