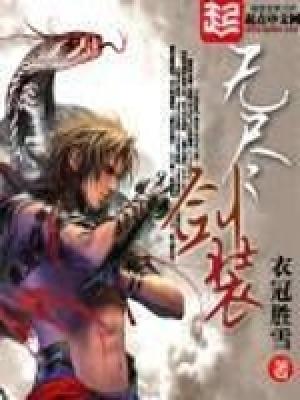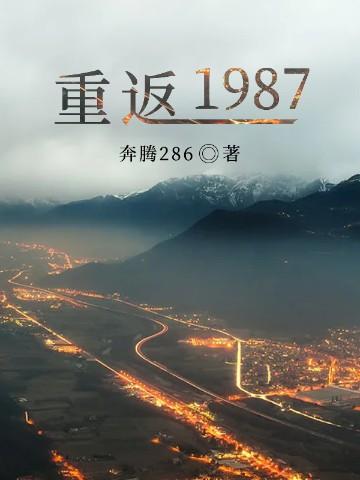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婚后上瘾by聿战笔趣阁 > 第376章 陆 魏 带着情感亲他(第3页)
第376章 陆 魏 带着情感亲他(第3页)
两人同时怔住。
“你说……鸟?”聿战放慢语速,重复了一遍。
念安点点头,眼睛亮了起来,又试着说了一次:“鸟??飞??”
袁晨曦猛地站起身,冲过去跪坐在他身边,颤抖着问:“宝宝,你刚才是不是听见了什么?”
孩子不太明白她在说什么,但感受到她的激动,便笑着扑进她怀里,咯咯直笑。
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几天后,复健医生确认:念安已能初步分辨环境音中的高频信号,包括鸟鸣、风铃和儿童歌曲旋律。虽然语言输出仍处于萌芽阶段,但神经反馈显示大脑听觉皮层正在积极重建连接。
“这是奇迹吗?”记者在采访中追问。
袁晨曦摇头:“这不是奇迹。这是八百多个日夜的坚持,是一次次失败后的重来,是一个父亲跪在地上一遍遍重复‘我爱你’的结果。”
发布会结束后,她独自留在医院花园散步。夕阳西下,一群放学的孩子奔跑而过,笑声清脆。她拿出手机,翻到七年前的一段录音??那是她偷偷录下的,念安第一次对着摄像机咿呀学语的声音。
如今那段模糊的“啊啊”声,终于有了回应的可能。
当晚,她写下新的日记:
>“有人说宽恕是软弱,我说不。
>宽恕是最勇敢的选择,因为它要求你直视伤口,却不让它吞噬你。
>我们仍在路上,念安还在学着聆听这个世界,而我,也在学着相信温柔的力量。
>昨天他指着窗外的麻雀,第一次喊出了‘鸟’。
>那一刻,我知道,有些声音,哪怕迟到十年,也值得等待。
>就像那只风筝,线断过,修补过,但它始终飞向同一片天空。
>而我们,也在一次次坠落与升起之间,学会了如何相爱。”
深夜,聿战轻轻推开书房门,见她伏案睡着,便取过毯子盖在她肩上。桌上的笔记本敞开着,他瞥见最后几行字,久久伫立。
良久,他提笔在页脚添了一句:
>“如果你愿意继续写我们的故事,我会用一生去提供素材。
>不再是谎言、压制与缺席,
>而是早餐桌上的一句‘今天想吃什么’,
>是睡前共读绘本时故意夸张的嗓音,
>是每一次犯错后,真诚地说出‘对不起,请教我怎么做’。
>这就是我现在的野心??不做掌控一切的帝王,
>只做那个能被孩子安心呼唤一声‘爸爸’的男人。”
窗外,月光如洗,风筝在夜风中轻轻摇曳,丝线上新挂了一张纸条,字迹稚嫩却清晰:
>**“妈妈,花香。”**
春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