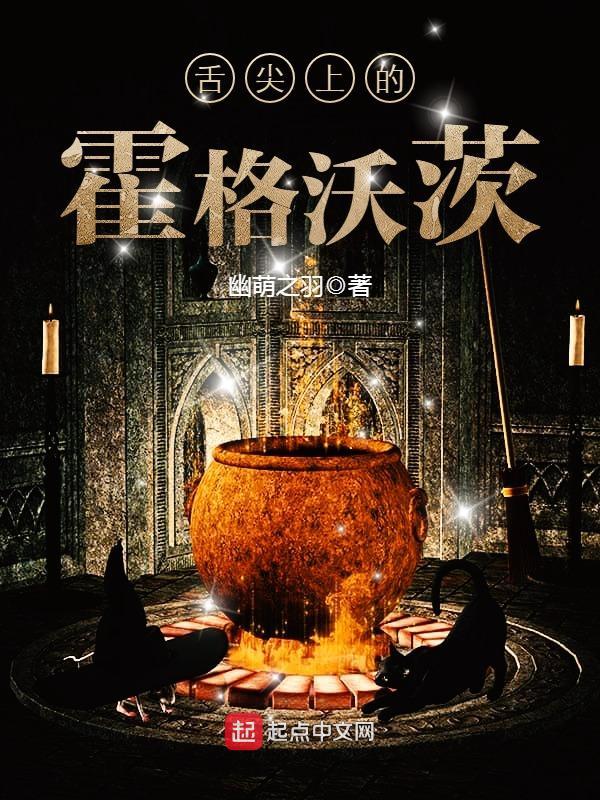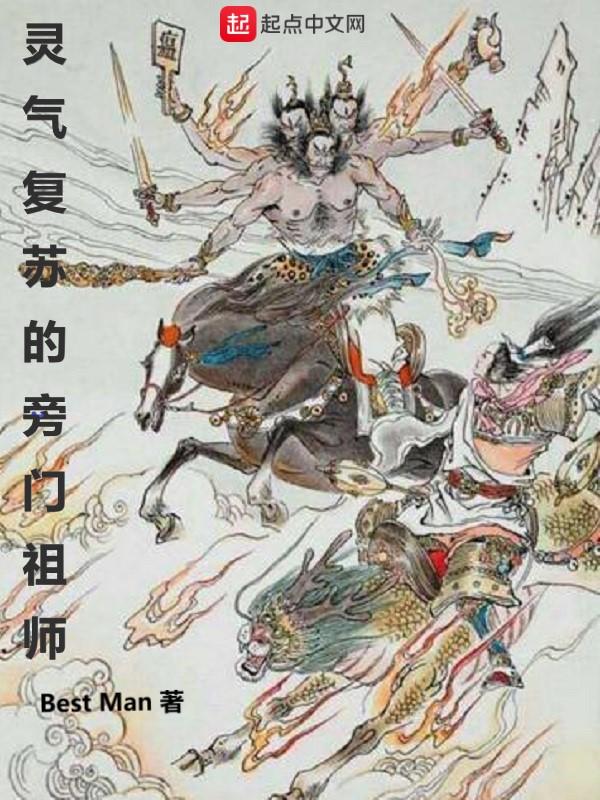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逆风笑 > 第42章(第1页)
第42章(第1页)
风啸天虚领着东海国中尉一职,江湖中却又执掌一方势力。这些年他行事,向来是借他人之手成自家之事——或递个消息,或指条明路,最多不过借些银钱周转。这次亦是如此。
他望着太守府送来的谢礼清单,唇角浮起一丝若有似无的笑。既让太守欠下天大的人情,又未在江湖上落下话柄。这般分寸,恰似他杯中浮沉的茶梗——多一分则苦,少一分则淡。
风啸天这般城府,想起自家儿子,眉间却拧起深深的沟壑。
“他的伤,可好些了?”
“回郎主,三公子目力已复七八分,只是”徐管家将茶盘轻搁在案。
“只是可惜了这身功力,”家主喉间一哽,叹息声沉得似浸了霜,“竟就这般折损了大半。”
他那日去了远风院才知,小儿子居然不惜损耗六七成功力,险些双目失明,也要保那个丫头周全。父亲怒子不争的喝斥声伴着茶盏迸裂的脆响惊飞了檐下春燕,袖中手掌几度攥紧又松开,最终化作一声震耳欲聋的摔门巨响。
风啸天指尖轻叩案几上的紫檀木匣,匣中静静躺着那枚“千风令”。窗外竹影婆娑,在他眉宇间投下深浅不一的暗影。他缓缓合上木匣。
“让子桓亲自给他送去。”
风啸天话音落下,徐管家微微一怔。他想起那日少主闯进啸风堂,控诉三公子以风神戟之力暗中护人通过试炼的场景。原以为家主会雷霆震怒,却不料少主反被训了个“无凭无据,妄断兄弟,枉为少主”,要他“莫要再提及此事”。然之后家主却又亲临远风院,率十二道风卫将远风院围得水泄不通,明摆的是不许三公子再去救人。如今这千风令又让少主赠予三公子——这一拦一放间,分明是要自己去唱黑脸,却暗中为这对冤家牵线搭桥啊。
可惜家主的苦心,只有他一个老奴看的清楚。
徐管家躬身接过那方紫檀木匣,眼角堆起笑纹:“郎主思虑周全,老奴这就去办。”
“他们兄弟俩啊”风啸天摇头轻叹,指尖在案几上敲出断续的声响,“嘱咐子桓,亲自带着他去千风阁,亲手将余容卷取给他。”
“喏。”
徐管家正要退下,忽觉家主目光微沉,不由顺着那视线望向窗外——恰是远风院的方向。老管家会意,试探道:“那个丫头?”
窗棂间漏进的夕照突然暗了暗,案上茶烟凝滞不动。
那丫头……
风谍早详细禀过云鸢试炼过程——轻功尚可,识毒之能倒是出类拔萃。虽说是碰巧被逍遥帮捉去、偷听到的密谋,但也算是处乱不惊、有勇有谋。若非他心存疑虑,倒真是个可造之材。
窗外竹影婆娑,沙沙作响,他凝视着茶盏中浮沉的青叶,恍惚间又见小儿子那双染血的眼眸。
风啸天和风家大部分人一样,握不住那把神戟——那一触碰时便如火灼针刺的滋味、被罡风掀飞的屈辱至今刻骨铭心。他从未参透祖传奇门阵法的玄机,也无从知晓以戟观局究竟要付出何等代价。但他记得,先父每次观局不过瞬息便汗透重衣。最久那次——为寻皇后安插的暗桩——先父枯坐了一个时辰,最终搜得一张风家布防图的方位。而后老人家便缠绵病榻,数月后溘然长辞。
念及此,他喉间发紧:相较而言,小儿子这次只是伤了目力、损了内功,倒是幸运了。
一声长叹散入茶烟。
这孩子自幼执拗,而今难得动情,若再硬逼,只怕
“让望月谷给远风院配药。”茶盏轻轻落案,惊起一缕檀香,“经过这试炼,他应该也摸透那丫头能耐了。罢了,就随他去吧。”
徐管家退至门口时,忽又听得家主一声叮嘱:“让子桓有点少主样子,管好自己院子里那条蠢狗。”
既做了这决定,风啸天也未再追究风延轩二度救下云鸢、坏了他借刀杀人之计的事,反而在家宴上亲自为二儿子布了一箸鲈鱼脍——二公子救人之事,终究化作盏中清酒一饮而尽。
只是风啸天始终不解,这老二究竟是如何在他眼皮底下办成此事的——虽说他亲自盯防的是三儿子,对这浪荡子确有疏忽,但护卫森严,这等消息本该更早传入他耳中才是。
面对家主的百思不得其解,徐管家心中早猜了七八分,只尴尬的欲言又止,最终耐不住家主的审视,只能讪讪道:“二公子应该是钻狗洞出去的。”
“什么?!”家主还不知自己儿子有钻狗洞的习惯,只怕是听错了,又重复一遍道:“狗洞?!”
在之后很长时间里,家主一看见二儿子就会想起“狗洞”这二字。以至于琅琊王密信传到风家,家主心情复杂的拆开后,看到的竟是小公主要微服下榻风家,还点名要风延轩作陪,他额角青筋一跳,脱口而出:“皇宫的狗洞…你也钻过?”
风延轩耳尖泛红,领了命后匆匆拱手退出啸风堂。堂内霎时静了下来,只剩风延远垂首而立的身影。
“此事,你怎么看?”风啸天的声音裹着窗外的竹涛声传来。竹影婆娑,将家主复杂的神色切割得明暗不定。
风延远眸光微动:“皇后素来谨慎,允公主微服私访…不似她作风。”
“不错。”风啸天指尖轻叩案几,发出沉闷的声响,“公主此番到访,须得谨慎应对。”他忽然话锋一转,“安排个伶俐丫头随侍左右,也好让贵人领略些民间风物。”
“喏。”
风啸天见他恭敬,问道:“她的案宗,你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