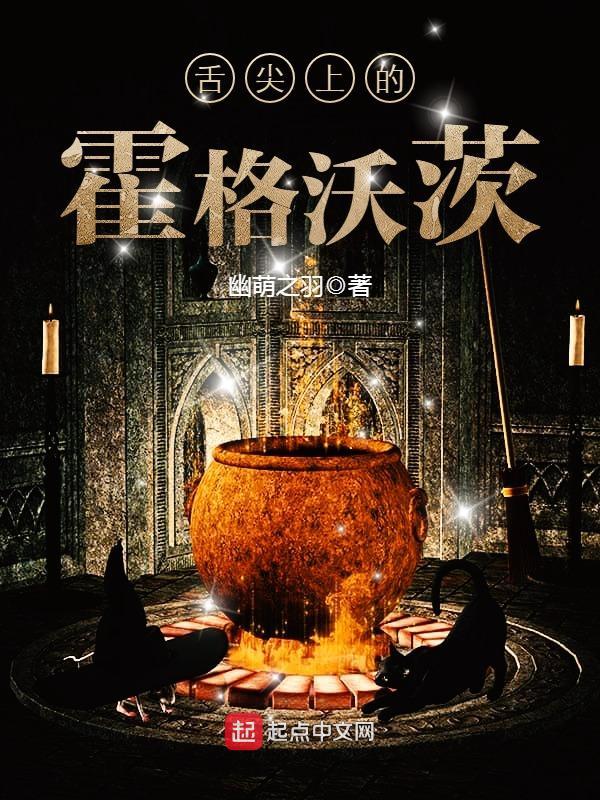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是我哥僵尸嬷嬷 > 1第 1 章(第2页)
1第 1 章(第2页)
宝诺使了牛劲,脑门抵住他颈窝蹭,像要蹭掉一层皮似的。
“你这次走了快三个月。”她皱眉控诉:“三个月!”
谢知易低低地笑起来,把她放回床铺,可手松了却没放得下去,她的四肢还牢牢束紧。
“不冷吗?”谢知易长得高而结实,宝诺小时候觉得他像大树,攀上去可好玩儿了。他手往后,握住她的脚腕探了探体温:“快回被窝,你这几日不能受凉。”
听见这话,宝诺也没怎么臊,倒是钻回铺盖里:“哥哥怎么老记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
谢知易将那碗红糖生姜饮端给她:“你的事都很重要。趁热,先喝了。”
宝诺接过,三两口喝完,随手把碗放在三角几上,又将灯台从枕边拿开,接着往里挪,拍拍床铺:“躺进来,我有好多话和你说。”
谢知易想了想,听她的话照做:“明儿除夕,过完年你就十五岁及笄了,怎么还像小孩儿似的。”
宝诺自有道理:“哥哥也过弱冠之年了,怎么还跟我计较?”
谢知易语塞片刻:“也对,你在我面前永远都是孩子。”
一只手从袖子里伸过来,扯他衣裳。
“怎么了?”
她眨眨眼睛。
谢知易登时领悟,稍支起身,凑近她热乎乎的脸颊,两人亲昵地蹭了蹭鼻尖。
这是他们之间私密的小动作,再怎么闹脾气吵架,只要这么贴一贴,气息交缠,即刻便能找回小时候相依为命的感受,骨肉至亲,血脉相连,他们是这世上最亲的人。
谢知易说:“你知道吗,有些猫儿到一个地方便要到处蹭蹭,留下它自己的气味,标记地盘。”
宝诺扬眉感叹:“有的猫却爱往外跑,不着家,三不五时地跑个没影,都快成野猫了。”
谢知易支起胳膊托着脑袋瞧她:“嘴皮子愈发刁钻。”
宝诺抬手,食指指尖点着他的额头,一路往下,经过远山俊峰般的眉宇,从笔直的鼻梁滑落。
谢知易闭着眼睛享受。
“哥,你这次走那么久,我做噩梦,梦见你再也不回来,把我丢下了。”宝诺喃喃地说。
谢知易一怔,将她的手抓住:“傻子,做这种傻梦。”
“我是傻子,那你就是大傻子,大笨蛋。”
谢知易那双漆黑的瞳孔晃了晃,扬眉莞尔:“目无尊长。”
宝诺朝他挪近些,感觉熟悉的体温和气息将自己包围,好像雏鸟回到大鸟羽翼之下,如此安全,如此体贴。
“瘦了好多。”她低声轻轻地:“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休息?”
谢知易心里泛起微弱的叹息,稍纵即逝:“我很好,只是赶路顾不上饮食,怕来不及陪你过除夕。”
宝诺皱了皱鼻子:“那你还记得走前答应我的事么?”
“当然,过年教你骑马。”他想起什么:“但这两日不行,等天晴了再说。”
宝诺笑得眸子发亮:“哥哥说话算话。”
“那是自然,我什么时候敷衍过你?”
宝诺与他聊至深夜,直到眼皮子快睁不开才恋恋不舍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