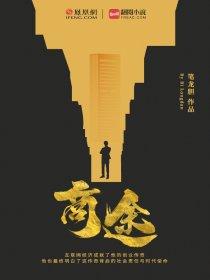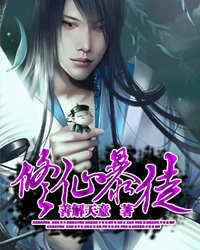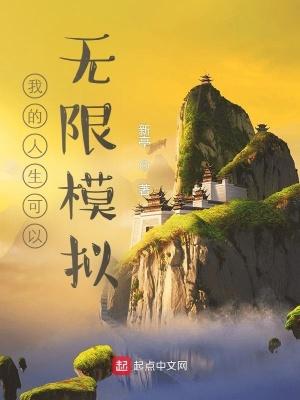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帕米尔的风网络 > 第24章 舌战(第1页)
第24章 舌战(第1页)
第24章舌战
在喀什的餐席上,吴娥感觉到艾米丽是一个健谈的女子。当然,这是由于三路人马偶然遇合,有太多需要交流的问题与交换的信息。如果不是男友的碰肘提醒,估计整个晚上艾米丽会把聚餐变成讲座。事实上,虽然艾米丽是东道主,但主要是劝人用餐,自己在餐盘前只是轻描淡写。
从有限的几次餐具起落来看,吴娥明白,艾米丽是在控制碳水化合物,为此对手抓饭、饺子、汤油之类食品自动绝缘。这是当代女性共同的难题,就是克制食欲保持身材。
吴娥也注意到,柯克纸一改过去少量进食的习惯,而是大快朵颐,像是新疆让他豪爽起来。吴娥还不知道柯克纸体能测试受到的刺激,是警队生活和晨跑习惯,也让他不能延续码字生活养成的久坐少吃作风。吴娥暗想,柯克纸以前码字和节食,是不是一直受到艾米丽的影响呢?
吴娥也简单吃了点东西。她早就在等待用餐时间的结束,从而大家离席退到茶座前,痛快地聆听相逢背后的故事。吴娥首先想了解的是,艾米丽为什么会出现在塔依尔的牧场上。当然,基本原因已经弄清楚了,这是上海有组织的采风活动,而艾米丽正好把这些网络作家引向了自己的野心,就是为让让《玛纳斯》借“网文出海”,不断地在南疆采写玛纳斯奇。
就是说,目前看来,寻找玛纳斯奇,比寻找风筝男孩还更让艾米丽兴奋。吴娥暗想,如果老扎拉尔所教的那个异乡孩子就是风筝男孩,这两种追寻正好可以合而为一,三路人马完全可以再次结盟,趁国庆假期再进牧乡。只是在谈及这个问题前,大家还得聆听艾米丽把她“舌战群儒”的经历叙述一遍。毕竟,东道主有说话的主导权,何况这也是大家想听的问题。
果然,艾米丽喝了口茶水,又开始了讲述。她说,那场“舌战群儒”的座谈会让她终身难忘。她所说的“群儒”,是一群杂志的编辑。
2022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文化润疆行动五年计划》。此后,沪疆之间文化资源双向奔赴,交流交往丰富密集。比如新疆文化入沪,有专题音乐会、喀什风情展、主题巴士线,有快闪体验、喀什画展。当然上海奔赴喀什也是题中之义,诸如上海文化周、企业家考察、轻音乐边疆行,层出不穷。当然还有部门的单向交流,一大馆建的“初心驿站”,援疆干部建的“江南书局”,以及各种非遗保护、文旅互动,让上海与新疆互相看见、互相融合。
其实,上海自2010年就开始对口支援喀什,主要对接泽普、巴楚、莎车、叶城四县,当然,我知道江西对口支援的阿克陶县,上海的任务更多,但以前也主要助力经济建设,而文化这块做得不多。去年秋天,上海组织了十多名作家到喀什采风,两地作家还举行了座谈会。在会上,上海方面的同志表示,上海县级作协的杂志也是优秀的文学期刊,考虑推介喀什优秀的文学作品,还可以通过网络开展诗歌朗诵会,此外将在人才培养、精品创作、作品刊登方面继续加大合作力度。
我呢,既是上海的文青,又是喀什的作者,我曾经是传统作家,上海的杂志当然是我的重要读物,毕竟上海是文学的重地,先锋作家和大牌刊物让人敬重和心仪,但我上刊无门、落草江湖,成为了一名网络作家。为此,喀什的兄弟姐妹叫我参加座谈会,我感觉自己不是同一路人,起初不愿意去,但又经不住他们怂恿,说是无论如何得见见家乡人。
我当然默默坐在最后。听到上海县级作协杂志推介喀什作家,我不禁有些感冒,为什么上海的大刊物不能来培养基层作家?我当然清楚,底层作家还不够级别、还不够实力,但培养就是培养,为什么要讲级别?不是说人才培养吗?最后,主持人让我们提出问题和建议,我就递了张条子,问,上海的网络文学非常发达,什么时候组织网络作家来新疆采风。
谁知,一位作家兼杂志编辑听到主持人念纸条,说,网络文学?那就是垃圾,整体上拉低了文学的审美。
要知道,我当时听了非常难受。这位老师本来就说过一些雷人的话,让我听了非常不舒服。当时喀什作家提供了一些作品,让上海的老师来指导,这位老师看到是乡村题材,就说,写农村的?农村有什么可写的呢?就那些事儿!但这作品不是我的,我听听就算了。
听到她非议网络文学,我就不禁站起来询问。我问,网络文学是垃圾?那现在国家支持“网文出海”是错误决策吗?难道这是垃圾转移?
老师们听到我反驳,有些意外,说,网络文学跟我们不是一路人,那些东西都写些什么呀,穿越呀,玄幻呀,一点儿不严肃,是没文化的人看的,就像现在火起来的手机短剧。
我听了,更加火气,我是孤身作战,但我不容这样任意褒贬。在作家圈不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写小说的嘲笑写诗的,写散文的说小说穷途末路了,写诗的说只有诗歌是皇冠上的明珠,小说散文根本就不是艺术,写古体诗的又看不起写现代诗的,你看,互相瞧不起,这就是所谓的文人相轻。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界,他们津津乐道,采风的作家都是传统作家,根本没人看过网络小说,不清楚网络文学。
会场上正响起一片嘟哝。来宾们以嘲笑的表情互相打听,互相逗笑:你看过网络文学吗?你读过网络小说吗?我又不是小孩子,看那个看嘛?我刷过,错别字一大堆,不花脑子的,就是消遣而已。
我不管他们的议论,继续替网络作家说话。我说,你们这么瞧不起网络文学,但你们知道吗?网络写手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网络文学”这个概念,就是写作的,就是为读者服务的,“网络文学”是你们炮制的概念。另外我要问,当年那些剧作家,关汉卿呀、阿里斯托芬呀,他们把戏剧搬上舞台呈现给观众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搞文学,只是要为观众服务,你们说他们不是文学家吗?
这时,他们开始有些惊讶。有一人说,他们当然是文学家,是开创者!
我继续说,当前最有活力的文学在网络,你们看纸刊有多少订户呢?编辑自己都说,我们辛辛苦苦办刊物,又没什么人读,现在的杂志呀有上万户的订阅就是不错的业绩吧?但网络文学呢,作品上新时,起跑线就得两万,否则作家就会放弃,没法养活自己啊!
我当然听到了会场的反驳:流量不能说明什么,艺术是小众的。
我继续说,流量有什么不好?在遵守法律、尊重公序良俗、遵照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经济效益就是最好的社会效益。网络作家为什么没有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概念呢,因为这只是载体不同,你们办纸刊,他们搞网站,但都是文学,都追求“爽点”。
我听到了会场上的嗡嗡声:传统文学,严肃文学,阳春白雪,不可相提并论,我们追求审美,不是追求“爽点”,这是娱乐至上、娱乐到死,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不符合文以载道。
我听不清谁在说。反正他们都一样。他们早就不屑一顾地在闲聊。我把所有人视为靶子,准备好好演说一番。我不怕这样的冲动有违两地作家的友好作风。我说,你们知道什么叫“爽点”吗?会场上,响起轻微的笑声,大概“爽点”一词让他们有了什么不良想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