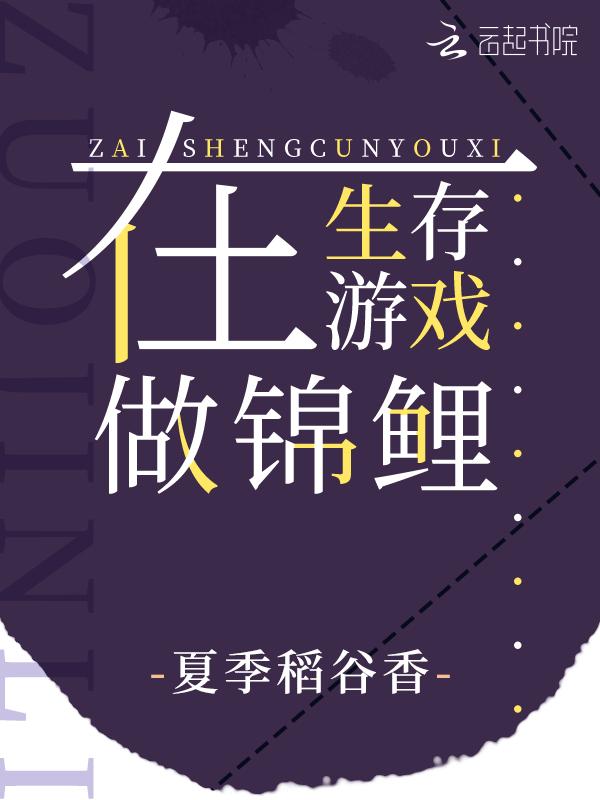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少夫人训夫手札by拥风听月 > 2推杯道是非谎病欲推拒(第1页)
2推杯道是非谎病欲推拒(第1页)
严问晴的堂婶在老宅住了三天,闹得人仰马翻。
原本井然有序的内务因这位妇人频繁指手画脚弄得手忙脚乱,许多习惯了上行下效、事半功倍的仆从这会儿失去条理,搞得身心俱疲,忍不住私下抱怨。
严娘子向来说一不二,那样雷厉风行的人,怎么纵着她的堂婶在祖宅这般放肆?
堂婶倒是待得舒心极了。
她只觉得祖宅真是块风水宝地,连仆从都这般懂事听话,难怪严问晴能管得好这方祖产,若是她手下都是这样乖觉的仆从,又哪里愁中馈繁杂?
又过了两日,一封拜帖送到严家。
是李家杜夫人不日登门来访。
堂婶前几日听严问晴说过有定亲的意思,猜杜夫人这是打算上门相看,再想到严问晴父母双亡,作为长辈不由得生出几分当家人的心思。
于是迎客那日,堂婶径直越过严问晴,似主人家般上前寒暄。
杜夫人却美目一转,定在门前落落大方的姑娘身上。
“严娘子。”她朝清丽的严问晴微微颔首。
严问晴方上前一步,朝她福身见礼。
堂婶叫她们冷落一旁,有些挂不住脸,又凑上去笑道:“我这侄女父母双亡,身为她的婶娘,当代为招待客人。杜夫人里边请。”
分明已经道出身份,杜夫人却不接她的话茬,依旧看着严问晴道:“这位是?”
严问晴不冷不热地答:“是族中堂叔的妻子。”
杜夫人点点头,终于正眼看堂婶。
只是不待堂婶挂上笑寒暄,便听她问:“不知尊驾功名几何?在何高就?”
堂婶磕巴了一下。
她支吾道:“没什么功名,不过做些海上的买卖。”
杜夫人面不改色,堂婶却觉得她噙在嘴角不变的笑带着刺眼的讽意。
严家是祖上冒青烟出了严问晴祖父这样一个大官。
可恨老爷子沽名钓誉,年轻时还凭职务返乡相看过几回族中子弟,但也不过是做做样子,为官十几年不曾提携过同宗的年轻人,生怕叫人抓住把柄。
他一走,严家更是捉襟见肘。
堂婶想到自己相公屡屡抱怨当年老爷子看着他皱眉摇头的模样,越发觉得面前这两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家伙面目可憎。
不过是投个好胎,长在京兆,凭什么自命清高?
她咬牙笑着:“犬子倒是读了几年书,先生屡屡夸赞。”
虽考不出功名,怎么着都比家里没儿子、有儿子还不如没儿子的人家强。
可杜夫人和严问晴神色如常,直教堂婶似一拳打在棉花上。
堂婶不敢思杜夫人的不是,遂在心里暗骂严问晴真是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同外人一唱一和折辱自家人。
及至迎客入堂,侍女奉上茶汤。
堂婶又忙不迭道:“这是紫笋贡茶,夫人好好尝尝。”
杜夫人笑容淡了几分,放下手中茶碗,微打量堂婶几眼后道:“夫人客居于此,倒是对种种情状如数家珍。”
堂婶听出她平淡语气下的讽意,悄然瞥了眼严问晴。
见严问晴垂眸不语,与五年前牙尖嘴利的模样截然不同,不知是这些年沉稳内敛了,还是在未来婆母面前做做乖顺的样子。
不过严问晴的态度叫堂婶心下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