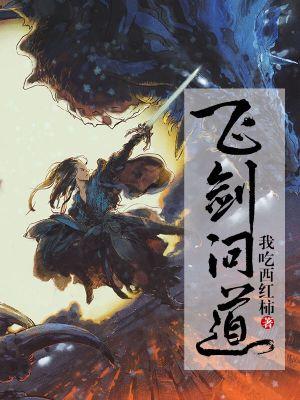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买活全文免费阅读 > 950960(第7页)
950960(第7页)
越是扯那些虚头巴脑的,越是有得辩驳,可当话题来到如此浅显直白的层次时,反而没人能反驳什么了,绞尽了脑汁,也只能期期艾艾地挤出一些蹩脚而软弱的辩驳,还有些人是直摇头的,认为皇帝是遭了心学和买地新学的毒害,“怎么把民贵君轻给歪解了!”这些人在平时反对皇帝的时候,是把‘民为贵,社稷次之’挂在嘴边的,认为敏朝删节《孟子》,淡化这个论点是‘君主之私’的表现,该被批倒,但现在却又对这句话嗤之以鼻,认为皇帝赞成这个观点是忘了本——本朝的老祖虽然尊崇孔孟朱,但对这句话却是十分不以为然的,皇帝没能和他保持一致,在儒家传统的价值体系里,便是‘大不孝’!
秉持这样观点的人,为数是相当不少的——这从一件事可以看出来,那就是这番对话虽然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京城民间门流传了开来,但对话的详细内容却经过篡改,这样,虽然京城这里也出现了‘正统转移’和‘正统仍在’两个派别,这样使得矛盾依然保持在儒门内部体系之中,买地新学则依旧毫无存在感,保持着其在敏朝文坛特有的一种被忽视的状态:
这学说的确是存在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敏朝文人一度试图从纸面上将其驳倒瓦解,但一旦发现纸上谈兵毫无作用,买地道统生机勃勃,还有‘张犬’这样的癫子为其鼓吹,似乎还真辩论不过,且自己的战友逐渐南下,力量日益单薄,甚至连江南文宗都悄无声息,似乎也跑过去换了一个名号,混得风生水起了。这些北地仅剩的抵抗力量,便逐渐敛旗息鼓,改为采取忽视的态度,就当它不存在一样,装聋作哑,连架都不吵了,甚至连这样确有其事且影响重大的辩论,都能给扭曲在自己的圈子里,绝不会给新学一点眼神。
要说这股抵抗力量是自欺欺人么,可它们残存的能量仍是相当惊人的,哪怕连皇帝亲自下场,想把对敏朝道统的争论,放到台面上来,都是碰了这样不大不小的一个软钉子。冷眼旁观的买地使团馆长谢向上,把这件事定性为皇帝的又一次尝试,他在写信汇报时谈到了自己的看法,“或许皇帝也很清楚,这些旧学臣子的命脉就在于他们的正统性,正统性决定了儒学进士对官僚晋升渠道的把持,迄今为止,高层官僚依然牢牢地把特科进士排挤在外。而皇帝的一切举动,都是试图在这道铜墙铁壁上撬开裂口,把特科进士送进这个封闭的圈子,在思想上更加亲近买地道统,也是他和儒学进士博弈中所刻意显露的姿态。”
“但是,哪怕妥协了让他参加定都大典,旧科进士在这件事上也不会有丝毫让步,民间门传说和事实的偏离,便体现了它们的倾向,或者说,也是旧科在如今的大势中最终展现出的态度:改朝换代是无法阻拦的,但他们的底线是,买地的新朝也要给他们的学说留下位置,哪怕是较次要的,大宗小宗中屈居小宗的位置,但儒门还是要保留独立的地位和完整的传承。否则,他们将会拒绝一切沟通和媾和,一心一意地顽抗到底……”
一件小事,直白点说,就是皇帝要闹脾气去参加定都大典这样的荒唐事,竟能解读出如此复杂的政治博弈内。幕,旁人看了,恐怕都觉得谢向上有些多虑,但谢向上对此却相当的认真,他仔细地解读着皇帝的心态,“皇帝的要求中也不无赌气的成分,他的性格有其复杂性和分裂性,一方面,他是个单纯而有几分天才的建筑家、工程师,另一方面他又从小受到培养,是个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政治家,也承担了宗族长男的担子,有受到传统礼教束缚的一面,有作为帝国皇帝而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自然产生的野心。”
“在皇帝的职位逐渐更加艰难,手中实权渐多而担子越重的时候,时不时他也有撂挑子的想法,这就是建筑家的一面出来作祟了,但政治家的一面也并未远离,参加定都大典,他最大的意图应该还是想看看新式审美所建立出的电气化城市,以及新的建筑潮流,但政治家的一面也让他把自己的欲。望当做筹码,和臣子们讨价还价,试图把国家往他意图中的方向带领。在政治家的一面来说,皇帝应该基本完全摆脱了儒学的影响,彻底皈依了买地道统,这一点,从他对藩王宗室的处理就可以完全看出来了,一个封建君主,只要还存了一丝老式统治的逻辑,都不会对宗亲如此狠辣,他总还要指望他们去治理地方的……”
这是一封船递快信,不是通过电报传递的简报,因此可以写得尽量详尽,谢向上把他对皇帝的了解和揣测都仔仔细细地写在了信里,也尽量去分析皇帝成功参加定都大典的利弊和后续影响,不过说实话,最后这部分他写得很吃力,因为他的确难以想象皇帝完全成为买地道统的信徒,并在敏朝现存疆域去推进买地的治理办法,同时和买地越走越近的后果,这是完全难以预料的,哪怕参照了如今欧罗巴的局势,都很难找到相似的例子来参考。两个本该敌对的国家,现在关系却如此紧密和友好,说实话甚至有点儿畸形,按照常理来说,此时双方都该忙于在大江周围修建防御工事才对,可如今却是亲如一家,合作救灾!
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敏买之间门会如何收场呢?他实在料想不到,就像是皇帝南下参加定都大典的后果一样,这是从前完全未有的事情。谢向上也不知道六姐对此的态度会是如何,他只能尽可能地把真实的情况传递到远方,包括京城这些年来的变化,皇帝南下诸多可能的动机——政治家方向的考虑,不敢说打包票完全揣摩清楚,但建筑家这面,绝对是强烈的动力,“本来他比稿输给了德札尔格,就有点不服气,看到信王寄回的彩画笺,感受到了德札尔格式新建筑的几何美感,就更想要亲眼看一看了。他说这是关系重大的事情:德札尔格的手笔,很欧罗巴,但皇帝不相信水泥砖房只能有这样一种审美方向,他认为塑造一种新的,符合传统美感,又能照顾到如今这些仙器发明的华夏建筑风格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需要时间门和经验,他认为这件事的关系也很大,甚至超过了当下的许多纷争……”
建筑——不管怎么样,无非就是住人的东西,它的影响真能这么大么?谢向上对此是不置可否的,某种程度,他似乎能体会到皇帝所谈论的那种超越了时代的传承,但其余时候,作为一个买地的干部,他又是非常务实的,对他来说,建筑能遮风挡雨,维持舒适的生活环境即可,当华夏还有许多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去在乎这建筑的审美是否有华夏气韵,简直就是精力的浪费——不过,无论如何,他也还是把自己的想法,包括如今京城的争论,一五一十地回报给了羊城港,等候着外交部的答复,他知道这不会是外交部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据谢向上所知,想参与定都大典的统治者,可不止皇帝一人,就连现在居住在建新的老酋童奴儿,都通过传音法螺传达了想参会的强烈意愿,因为信号的问题,这还是他这里给中继转达的信儿呢!
皇帝也还罢了,正当盛年,老酋这都多大了,还要坐海船……他儿子们也不劝劝,真就不怕在路上去了么?也不知道部里会怎么答复了……除此之外,南洋的、东瀛的、高丽的,甚至是欧罗巴诸国,非洲麻林地那块的酋长,若是知道消息,哪有不来凑个热闹的道理?谢向上之前还听说,果阿的白人也叫嚷着要派船来贺喜,甚至因为他们的关系,在果阿、苏拉特附近的身毒大邦,可汗也派了使者准备前来贺喜,这些人要都到了新京,光是接待和通译的活,就够部里喝一壶的了!
如果这些人都让来了,那不让皇帝去,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可皇帝要去,那麻烦可会超过这些人加起来的全部。谢向上一时也不知道部里包括六姐,会是如何决策的了,他还有个很荒唐的担忧:皇帝现在等于是又一次通过‘掀屋顶理论’钳制住了群臣,得到了南下的自由,谢向上很怕他去了南边就不想走了,或者,如果南边不让他去的话,他会乔装打扮,偷着去……
不过,只要皇帝离开了京城,理论上这就不是他的问题了,所以他的担心也并不那么牵肠挂肚,而做买地的吏目还有一点好,那就是上级的回复一般都来得很快也很明确,让他们在做事的时候能省掉不少担忧。甚至是在这件棘手的事情上,也是一样,一如既往地显示着买地,或者说是谢六姐特有的气魄。谢向上还是很快就收到了上峰的回答,非常简单,让他有理由怀疑是六姐的批示——
“来,都可以来!”
“他想来,就让他来!”
第958章恰可豆牛油小甜饼
“想要把新材料完全融入旧的建筑样式,也并非全不可能,传统多层建筑,亭、台、楼、阁、塔,都得益于竹筋混凝土技术的发展,引入玻璃窗之后,真正做到了宝相庄严、巍峨宏伟,令在高层建筑上居住的舒适性大大地提高了,尤其是水泥建筑的体量不受梁柱规格的限制,又可引入暖气、火墙等设计,令到屋内空间和舒适度的关系不再成反比,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尽量扩大房屋内室的尺寸,依旧确保良好的居住体验。”
“因此决不能说华夏传统建筑没有参与到水泥化的浪潮中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买地的城市化浪潮中,涌现出的大体量公共建筑的设计,依旧沿用了买地仙界的建筑传统,常见经过改易的大拱廊、高穹顶等设计来强调建筑的空间感,而这些设计拥有明显的异域色彩,可知在仙界中,或许是西方建筑先迎来了水泥化的浪潮,并且达成了从老式建筑到新式建筑的转化。需要注意的是,在买地呈现的新式建筑,以及教材中所接触到的建筑样式来说,新式建筑本身,和东西方老式建筑均有很大的不同,属于一种全新的东西,它只是在审美和排布上带有一定的西方色彩而已,而如今我华夏建筑界当务之急便是要发展出一种新的审美流派,将东方美融入新式建筑之中,探索出一条兼顾新旧的建筑设计之路。”
“新华夏建筑,不能仅仅是简单的在水泥建筑上加个重山顶,或者是简单地把现有的建筑等比扩大,这样的建筑仅仅仍旧囿于原有的功用,却无法满足水泥化、电气化,人口急剧扩张的新城市所需要的多功能大体量建筑,笔者个人愚见,就以京城中买地使馆超市为目标,有志于建筑业的能工巧匠、文人墨客,当以设计出符合我等原有的简明大气、严谨庄重的风格,又合乎诸般客人购物游览需要,使其感到行事便宜的设计为第一目标,填补如今华夏工匠在设计上的空白……”
不疾不徐的清脆念诵声,暂停了片刻,张九娘抬起头,从八仙桌中摆着的烫金盘子里,取过一片苦涩微甜的‘恰可豆’牛油饼,用门牙啃了指甲盖大的一小块下来,眯着眼惬意地品味了好一会儿,待得这油酥浓郁的芬芳充斥了整个口腔,饮了一口泡得恰好出色的龙井茶,这才轻笑了一声,换了个姿势,把双腿都缩到了牛皮沙发上,随意地点评道,“这个人,不知是不是传说中宫中的那位,又是不是在新京招标时献上图纸,还被采用过的那位,据说那个建筑师也是我们敏朝的宗亲,因此不愿泄露身份——你说这可巧不巧呢?”
“不过,不论如何,这篇文章倒是写得挺好的,用的白话,叫人看着舒坦顺畅不说,这里头的道理也是一通百通的,别说建筑了,就连服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华夏气韵,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又是那么的实实在在,买地的许多衣裳样式感觉就是没有华夏气韵,透着一股子西式的味道,尤其是那个衬衫,感觉就是给洋人穿的。当然了,胡服骑射,服饰又不同于屋子,一会儿时兴这个,一会儿时兴那个,也没必要那么计较,可话说回来了,见到人人身上都穿着那样的衣服,也怪别扭的。倘若大家都这样穿了,我们华夏的好料子,织出来又卖给谁呢?”
“是这个理不假。”她斜对过坐着的卫妮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过她吃零嘴儿的模样可比张九娘豪快多了,象棋子大小的小饼,她是一口一个,吃得满嘴咯嘣流香,还点评了一句,“你喜欢吃这个恰可豆的牛油饼,我却更爱吃薄荷味道的,吃起来清凉——以你这管织造的身份来说,也算是你的公务了,倘若人人都穿着那棉布素面的衬衫,叫这样好看的提花缎子做什么用处去?难道只用着做包袱皮、拿来当窗帘么?那也太暴殄天物了!久而久之,怕不是棉织品大行其道,丝织品暗淡落寞,那也怪可惜的。虽说这裤装的大方向是不好改的了,但形制改一改,料子改一改,把这华夏气韵再复兴一下,我这粗人都也觉得很有必要!”
“得了吧,卫姐儿,咱们可是同榜,你若是粗人,我们不都全成粗人了?”张九娘噗嗤一笑,晃着脚道,“以后你呀,说什么话可都得把咱们这一科的面子算在里头,别那么瞎谦逊了!”
“那不是在你跟前么,在别人跟前说这些,我可不是疯了?哎,我说,你喊我来,就为了读报纸给我听?”
“这不是商议着随团南下的事情么——咱们可说好了,在船上就住一间啊,我这人觉浅,你也不是不知道,你睡觉不打呼噜,我得赖着你睡,不然换了其余几个小陈、小李她们几个,那都是壮妇,一到晚上,呼噜震天,这船也别坐了,三四天我就得跳大运河!”
“就这事啊?”卫妮儿哈哈大笑,“你就矫情吧!到底是国公小姐,这话再别对旁人说了,不然,这才是带累了我们一榜的名声呢!我们这一榜也就你没出过京了,你但凡出去公干几次,这矫情病也被治好了!还打呼呢,老鼠就在你头顶上叫,累极了也是照睡不误,只要不来咬脚后跟就行啦!”
她形容的画面有点儿惊悚了,张九娘皱了皱鼻子,把九宫攒盒往卫妮儿方向推了推,意思也很明显——还堵不住你的嘴么?不过,卫妮儿说得倒也不假,从外形上,一看就知道两人过的根本不是一种生活,卫妮儿虽然年轻,眉头却已有了纹路,面上的风霜之色,双眼四射的精光,举手投足的气魄,在在都说明这是个手握实权,惯于发号施令的厉害人物。
而张九娘呢,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一双手水葱儿似的,浑身上下细皮嫩肉,也早已经不是多年前那走一步想三步,一点儿出格的事情不敢做,一句出格话不敢说那娴静谨慎的模样了,透着一股颐指气使的骄矜之气,这一看平素就是被人拍着捧着的过日子。要不是这两个女特进士,是同榜的交情,而特科官吏历来走动得紧密,真很难想象她们怎么能做朋友。
这也是因为两人在官场上走的路不同的缘故:卫妮儿入仕之后,一开始就是去京畿州县开扫盲班,那真是沉到一线去做事,后因为表现优异,被提拔去通州,主要走赈灾中转后勤对接,全是琐碎活,常年要和通州三教九流的人物打交道,她还是女官,必须精明外露甚至有点儿江湖气,这才镇得住场面。而张九娘呢,中进士后,虽然也去了州县,但她是国公府小姐,难道还真去睡稻草床?国公一家既然站在皇帝这边,安排张九娘出来考特科了,自然方方面面就能安排停当,又让人挑不出错,又让张九娘安安稳稳只管升官。
张九娘在州县上就住了半年,便因为政绩突出,回京进了织造局——别看她娇娇怯怯的样子,却也不是全靠家里,进了织造局之后,的确大展身手,因她别的不说,在服饰设计上的确有专才,织造成衣也是敏朝难得能返销买地的制造产品,否则,敏朝卖原料,买地卖产品,这局面完全是一边倒,敏朝衙门也是面上无光。在张九娘的带领下,织造局专攻名贵面料、手工缝制的买地成衣,也算是在买地的纺织品冲击之下,守住了自己的老阵地。她所上的几篇奏疏,也是特科制造业难得一见有亮点的工作报告,其中一些‘顺时而动,发掘自身优势’的话语,受到王良妃赏识,也被皇帝圈红,成为特科官吏必读,令她也颇为积累了一些政治上的声望哩!
国公府现在年轻一代由她挑头,后续陆续虽然也有人考特科,但表现不如她亮眼,因此自然对张九娘倍加呵护,张九娘专业能力虽然强,但工作之外的事情是可以一概不管的,这人心里想的事少了,物质条件又改善极多,自然而然就养得越发金贵娇嫩,且这些东西都是她凭自身本事赚来的——张九娘现在是入仕了,设计便都算是公用,倘若没入仕去买地工作,凭本事也一样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因此,她的金贵中更含了十足的底气,一个不承爵不起眼的九姑娘,现在倒有了点嫡长大小姐的味道……
她这新式的套房里,冷热自来水,上下水、淋浴、马桶、浴缸、暖气、玻璃窗、风扇、电灯、自行钟、大镜子,全都一应俱全,还有取代了贵妃榻的牛皮沙发三样式,这享受,真别提了,就像是把使馆超市的设施都在家里照搬了过来一样,别说京城,在买地都是最顶级的配置——别看京城现在市容和买地新京当然是无法相比的,但单单说这些奢侈品,两地的富裕阶层享受得还真都差不多,甚至京城的权贵条件还要更好一些,奴仆如云这不说了,便是屋子也要比买地富户宽敞多了。
买地富户没有园林,都和六姐看齐,‘户不私产’,这意思不是说真不许富户有私产了,而是说富户也不敢去营建过分奢靡的园林豪宅,风气还是较为朴素的。而京城,皇帝修了海清河晏园之后,陆陆续续,在清晏园附近的荒地,也有很多小规模的水泥化新式园林开建,这使得京城的水泥价格长期走高不下,这且不说,还有其余奢物,在京城的销路也是极好的,不然,这么常年的奢物买卖,也无法维持下去呀。
这两个特科女官,都是第一科就出来的元老了,虽然一动一静,外形做派迥异,但彼此的交情也是越来越好,因她们这一届,在官场上职位最高的就是彼此二人,就算一开始交情平平,这会儿也该抱团了。反而是一些原本刚中进士时往来频繁的姐妹,这些年下来,因为都在州县就职,通信不变,联系也是渐疏。不过,一般做客都是卫妮儿登门,毕竟她家不如张九娘,在国公府里独居两进小院,逍遥自在,如今也不过是堪堪在城里买了整院子,院子里还住了其余亲人。
她每一次上门,张九娘这里就能多添些新鲜物件儿,这一次就是两样特色的烤饼——听说这是仙界的食谱,连西洋人都没有吃过,虽然都叫小甜饼,但其中加了大量的牛油,吃起来油酥掉渣,和洋番所谓的小甜饼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洋番的甜饼虽然也加黄油,但要烤两次,吃起来硬得可以崩碎牙齿,都是拿锤子砸碎了泡牛奶吃,就和鞑靼人的炒米是一个意思,都是远洋航行的时候准备的干粮。
买地的这种油酥小甜饼,在京城的洋番也极为喜欢,又因为比起奶油蛋糕容易保存,在使馆一经推出就立刻风靡京城,据说在云县也广受各类洋番的欢迎,以至于洋番自己开的各种面包店,都争相抄录报纸上公布的食谱配方,还有人自行添减,在一些地方小报的厨艺专栏撰文探讨——消息一经传开,这几期小报又是身价陡增,京城的名门大户都在设法搜求,没办法,现在各地的小报实在是太多,而且还时不时的都有一些好文章,就譬如说这小甜饼干里添加‘恰可豆’,就是从小报里得到的方子,有没有看到这篇文章,还真的差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