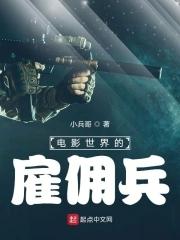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酥心蜜意(美食)莲子舟[玫瑰 > 贼见贼哭(第2页)
贼见贼哭(第2页)
大概有四十多年没有回平江府,王秋兰的目光落在周围,抹了一把眼尾的泪。
路还是那条路,这座拱桥,她少时一直和姐姐一起踏过。她们数过这边的青石有一共有几块,又在桥下捞起一篮子河虾。
一切都没变,又好像都变了。
新开了很多铺子,纵使有三两间还存在,那店内吆喝的伙计,也完全是生面孔。
招幡晃眼,伙计们在檐下热情招揽,客流如织。
各式各样的香气裹着新鲜出炉的热气,从铺子里,小摊的蒸笼缝隙里逸散而出。
“刚出炉的蟹壳黄,趁热来一块!要鲜肉、蟹粉、虾仁,还是糖芯、豆沙、枣泥。咱这酥皮是祖传手艺,三个铜板儿就能尝鲜,买回去给老的小的当零嘴儿,保管人人夸您会挑!”
小麻糕在垒好的石炉里烤得酥皮鼓起,伙计麻溜用竹夹拣上几个,塞进油纸,芝麻掉了满桌。
“酸梅饮子荔枝膏,紫苏水小豆汤,两文一碗就管饱,来一碗咯!”
“客官里边儿瞧!摸一摸咱这吴绫的手感,柔滑似春水,亮堂赛月光,穿在身上既体面又凉快,最是衬您这气派模样!您要做衣裳,甭管是襦裙袍衫,还是褙子半臂,咱这料子都能裁,价钱也公道!”
另一家铺子也不甘示弱,对门吆喝,“瞧瞧我们这绣了金线的水丝锦,逢年过节做身新衣,或是给娘子郎君添件衣裳,才叫个精致体面!咱这都是老主顾口口相传的好货,童叟无欺!要不您先挑块料?”
这一路的叫卖声给卫锦云听得一愣一愣,看来要在这偌大的平江府市井立足,光吆喝还不够,还得吆喝得劲。
人人都是一张利嘴。
吆喝声,车马声,隐约的琵琶丝竹声不绝于耳,行人多得数不胜数,衣饰光鲜的,轿子马车的。。。。。。
“菱姐儿过来,吃碗汤饼。”
王秋兰在一家汤饼铺子的招幡处停下。这招幡上的“钱记汤饼铺子”几个字已经褪色,连幡面也泛起黄边。相对于方才的吆喝,这家铺子倒是没有伙计在外。
然桌椅从铺内摆到外头,坐满了行人脚夫。
几人等了一炷香的功夫,才给腾出一张小桌。
卫锦云麻利地给姐妹二人添碗倒醋,让王秋兰玩笑几声是不是她梦里来过,怎的这么娴熟。
他们才坐了几日的船,一路摇摇晃晃,在运河里,雨季并不好走。纵使卫锦云变着法子做了些吃食,姐妹俩个也是在船上过得晕乎乎的,没吃多少东西。
“吃碗汤饼,能让肚子舒服些。”
卫锦云揉了揉卫芙菱东张西望的脑袋,“听祖母说那铺子几十年没动过,想来一进去不能立马开锅,要好好收拾收拾,我们先在外头吃了。”
王秋兰的铺子就在不远处,再拐个弯就倒了。这家汤饼铺子的面她从小吃到大,没想到几十年过去,它依旧在。
本想一鼓作气回铺子,到了这儿却依旧忍不住停下。
伙计掀开后厨的竹帘,端出几碗冒着热气的面。
隐隐还能瞧见灶台上锅中咕嘟作响,师傅甩将面团甩在案板上,细如银丝的面条在拉扯间被抖落进滚水里。
“眼下这什么都涨价,唯独你家这汤饼铺子几十年如一日,老钱,你不怕亏本啊。”
食客拌好自己的面,扯着嗓子笑道。
“亏倒是不亏,小挣也是挣嘛。”
里头揉面的那位师傅回应,“还得靠你们撑场面呢,大家伙挣钱都不容易。”
几位食客笑着攀谈,铺子里处处都是“呲溜”声。
平江府的面讲究浇头,碗里卧着雪白面条,浇头色泽鲜亮,装了好几个碟子。
鳝丝焖得透亮,焖肉肥瘦相间,煎蛋也要单独摆个盘,还有一碗剥了壳的虾仁。
几人点了三碗,卫锦云与王秋兰各一碗,姐妹二人单独用小碗分一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