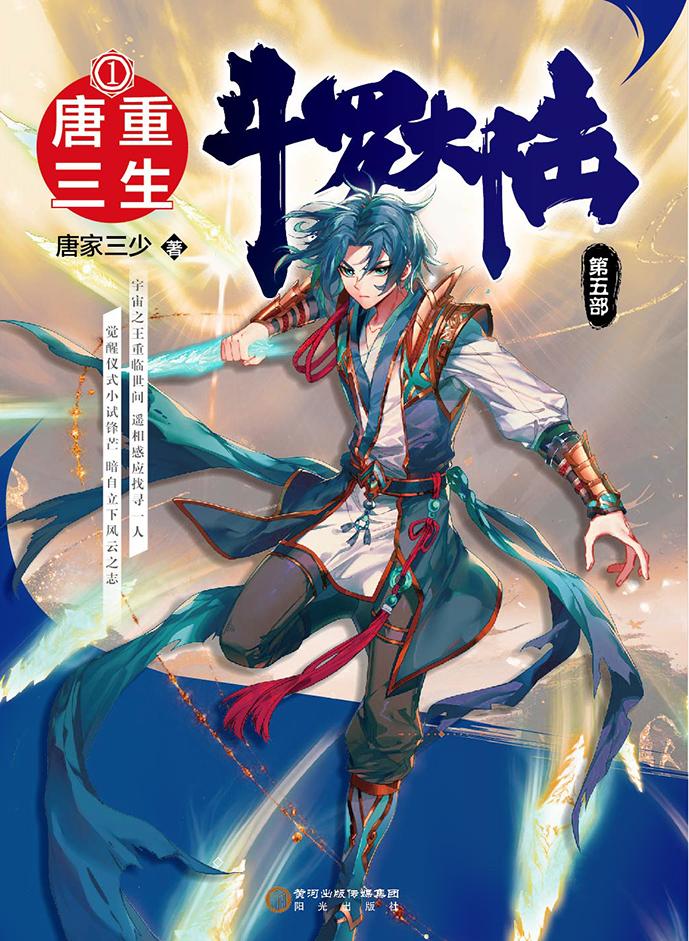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草木青是什么意思 > 天上月(第2页)
天上月(第2页)
她看着靳杨在一旁安静地等所有人都落座后,如愿坐在她身旁。
电视机里放的春晚早成了他们谈话时的背景音乐。
谁举杯提议,谁又抬头一仰而尽,在一片爆竹声中,彼此共同祝愿明年越来越好。
酒过三巡。
靳杨起身,端着刚煮好的茶,走过去往长辈们空了一半的茶杯里添。林荞抬头,林伟民坐在主位,右手边是靳叔叔。
果不其然,父亲见此又开始夸他。林伟民称赞靳杨稳重懂事,又有眼色,末了还让她多跟着他学学。
学什么呢,添茶倒水的活,她以前竟是从未做过。
她心里尴尬,面上却不显,欲起身接过靳杨手里的茶。
他却向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她,他并不需要。
“以后这种场合丫头都不用动,让这小子自己一个人忙就行。”靳文礼的话刚落,靳杨便绕到她身边,往杯子里添茶。
香气清雅,温润细腻,带着微微的焙火气,之后是若隐若现的果子香。
林荞笃定,这是父亲带来的金骏眉。
可惜她不怎么爱喝。
她这人挑得很。不喜欢香气单一,滋味柔和的茶。非要说的话,或许只有凤凰单丛算个心头好,可惜没几个人知道。
她习惯了“随大流”,林伟民从小便教她,要学会“藏”。
-
饭局接近尾声,她已经累得腰酸背痛。
林荞坐得笔直,为了显得文文静静,整晚后背都没来得及和椅背来个亲密接触,屁股只占了椅子的三分之一。
她的腰不能久坐,站久了也会不适。
后来她自己偷偷去医院看过,医生说这是从小落下的毛病,治不了,但生活也没什么大问题。
那要追溯到林荞小学的时候。
她那时放学后不能直接回家,而是等着林伟民的警务员来校门口接她,他们直奔家附近的舞蹈教室。
那时候小女孩流行学跳舞,大家都说学古典舞的女孩长大了一定气质好,林伟民夫妇一听,二话不说就花重金给林荞报了个舞蹈班。
但林荞的天赋并不好,她曾经不好意思地跟爸爸妈妈开口,说自己不想去了,实在是腰疼得紧。可每次得到的几乎都是相同的答案,他们说“为什么别人能做到你不能”“多练几次就好了”“人要学会坚持”……
后来她就闭嘴了。
每天下午五点,林荞都默默做好心理建设,咬牙把自己卡进舞蹈室的把杆里。她整个人先要刻意地放松下来,然后舞蹈老师趁她身体最松懈的一瞬间,毫不留情地拉着她的手往下一拽。
她的指尖擦过脚踝,有时是刚刚碰到。
下一秒,腰间“咔”地响了一声。
林荞觉得她身体里有一块骨头在用它自己的方式提出抗议。
可惜,没有人理会它。
她学会了沉默。
林荞每次都趁大家举杯时将手指绕到后腰处,轻轻揉两下。直到第三次,服务员拿了个靠垫走进来,“这是您刚才要的。”
林荞:刚才?
刚才窗外的雪停了。
靳文礼招呼着靳杨,带妹妹去放烟花,“我车里有,早上你王叔刚给我装的。”
靳杨上下打量了一下林荞今日的穿着,露出狐疑的眼神,“你这身,能去放烟花吗?”
“可以呀,我和你去。”
这意味着能出去放放风,喘口气儿。林荞早就想逃离家长的视线,匆匆答应他。“走吧哥哥。”
林荞跟在靳杨身后,走到门前的小院里。
靳杨让她原地等着,自己先去车上把后备箱和后座所有的烟火都搬到面前的空地上。他记得早上是李叔叔还是赵叔叔来着,搬上车时还提了一嘴,这些烟火能放到大年初五。他那时没在意,现在索性全都卸了下来,当一口气儿听个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