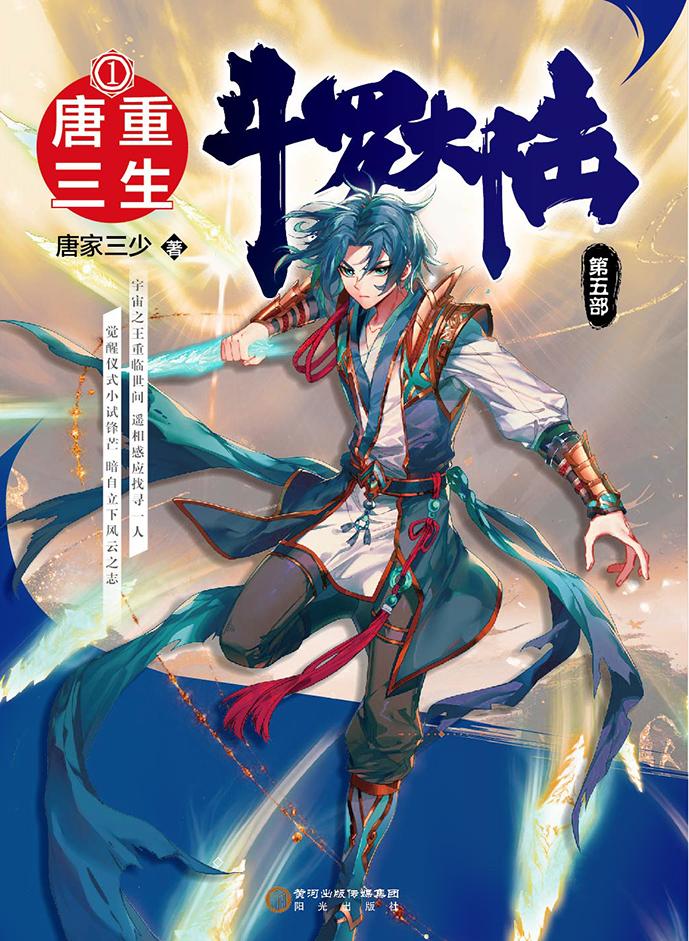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太子竟然暗恋我 > 赠礼(第1页)
赠礼(第1页)
手背上的水泡结痂时,左忆终于把《女诫》背全了。张嬷嬷拿着戒尺,逐字逐句地考她,听到“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时,特意顿了顿:“记牢这句话。太后娘娘让你读书,不是让你学那些酸儒掉书袋,是让你懂分寸。”
左忆垂着眼应“是”,指尖却在袖袋里蜷了蜷。她想起前世解剖室里的《法医病理学》,书页里夹着的批注比正文还密——那时没人告诉她“不必才明绝异”,只说“错一点就是一条命”。
云袖来送宁心丸时,见她对着窗外出神,顺着她的目光看去,院角的梅树底下,不知何时落了只死鸟,羽毛沾着泥,僵得像块石头。
“姑娘别看了,我让小桃来扫了。”云袖把药丸和温水递过来,语气里带着点嫌恶。
左忆却没接药,径直走到梅树下蹲下身。死鸟是只灰雀,翅膀张着,一只脚蜷在腹下,看姿态像是被什么东西啄断了脖子。她伸出手指,轻轻碰了碰鸟的眼睑,冰凉坚硬——死了至少半日了。
“姑娘!”云袖吓了一跳,赶紧过来拉她,“这脏东西有什么好看的?仔细沾了晦气。”
左忆没动,指尖顺着鸟的胸腔摸下去:“它肋骨断了三根。”
云袖愣了愣:“姑娘怎么知道?”
“摸出来的。”左忆抬头看她,眼神亮得惊人,“左边第三根最明显,断口往外翘,像是被猛禽抓过。”
云袖的脸色白了些,往后退了半步:“姑娘……以前常看这些?”
左忆收回手,在裙角蹭了蹭指尖的泥。她想起解剖台上那些被水泡胀的、被钝器砸烂的、被利器剖开的躯体,那些藏在皮肉下的真相,比活人说的话可靠多了。
“在宫外见过。”她含糊地答,接过药丸吞下。苦涩感漫上来时,她忽然问,“云袖姐姐,太医院的人,是不是也这样看伤口?”
云袖的动作顿了顿,把空碗收进托盘:“太医院看的是活人的伤。”她顿了顿,又补了句,“姑娘还是少琢磨这些,别吓着自己。”
可左忆没听。当天夜里,她趁着月色溜到梅树下,那只死鸟还在,只是被夜露打湿了,羽毛贴在身上,更显狼狈。她从窗台上摸了块碎瓷片,是前几日练书法时摔的砚台边缘,锋利得很。
指尖捏着碎瓷片,她忽然想起张嬷嬷说的“分寸”。在孤儿院时,她用碎玻璃片划开过生锈的铁锁;在解剖室,她握着手术刀划开过七层皮肉。此刻握着瓷片的手却有些抖——不是怕,是一种陌生的谨慎。
她蹲下身,小心翼翼地用瓷片拨开死鸟的羽毛。月光透过梅树枝桠漏下来,在鸟的胸腔上投下斑驳的影。她屏住呼吸,像在做一场精密的解剖,瓷片沿着羽毛的纹理轻划,露出底下青紫色的皮肉。
果然,左胸第三根肋骨的位置,有个细小的凹陷,边缘带着不规整的撕裂痕。
“是被鹰抓的。”她低声自语。宫里有驯鹰的侍卫,她前几日路过御花园时见过,那些鹰的爪子弯得像钩子,抓着肉饵时,能听见骨头碎裂的轻响。
瓷片突然打滑,在鸟的皮肤上划开道细痕。左忆缩回手,指尖沾了点暗色的血——早凝固了,像干涸的墨。
“半夜不睡觉,在这挖什么?”
一个冷冽的声音突然从头顶砸下来,惊得左忆手一抖,碎瓷片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
她猛地抬头,月光正好落在来人脸上。石青色常服,腰间悬着块白玉佩,正是李承恩。他身后跟着的小太监举着灯笼,光打在他眉骨上,投下片阴翳,看着比白日里更冷。
左忆慌忙站起身,手忙脚乱地想把死鸟往身后藏,却被他一眼看穿。
“藏什么?本宫看见了。”李承恩的目光扫过地上的死鸟,又落在她沾了泥的指尖,“张嬷嬷没教你,宫里的污秽物该由洒扫太监清理?”
左忆垂着头,手背在裙角上使劲蹭:“臣女知错。”
李承恩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只死鸟看了半晌。灯笼的光晃了晃,照亮他眼底的神色,说不清是嫌恶还是别的什么。左忆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敲鼓,震得耳膜发疼——她忘了,这宫里最忌讳“不吉利”,尤其是在皇子面前。
“这鸟,”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夜风还凉,“是被海东青抓的。”
左忆愣了愣,抬头看他。
“侍卫房的鹰昨天没拴好,飞出来伤了好几只鸽子。”李承恩踢了踢脚下的石子,石子滚到死鸟旁边,“你看得倒准。”
左忆没接话,只觉得手心的汗把裙角洇湿了一小块。他怎么知道她看出是猛禽所伤?是刚才听见了,还是……
“拿着。”李承恩忽然解下腰间的匕首,扔给她。匕首鞘是鲨鱼皮的,沉甸甸的,砸在她怀里时,她差点没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