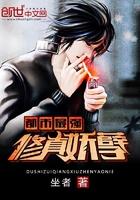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太子竟然暗恋我 > 青州信(第1页)
青州信(第1页)
去青州的路走了五日。
左忆避开官道,专挑乡野小路走,白日里在农户家讨碗水喝,夜里就蜷缩在破庙里歇脚。背篓里的药粉偶尔派上用场——给摔伤的樵夫敷药,帮腹泻的孩童配方子,倒也换了几顿热饭。
第五日傍晚,终于看到青州城的轮廓。青灰色的城墙在夕阳下泛着冷光,城门处往来的行商络绎不绝,比京城多了几分烟火气。
左忆找了家客栈住下,梳洗干净后,换上那身湖蓝色布衫,往县衙走去。她没直接找周县令,而是在县衙对面的茶馆坐下,点了壶茶,静静观察。
酉时刚过,一个穿着藏青色官服的中年男人走出县衙,面容方正,步履沉稳,腰间挂着块不起眼的玉佩。左忆认出那玉佩的制式——和李承恩送她的银针一样,刻着极小的“东宫”二字。
是周县令。
她结了茶钱,跟在周县令身后,见他走进条僻静的巷弄,才快步上前:“周大人留步。”
周县令转过身,警惕地打量她:“姑娘是?”
“故人托我带句话。”左忆压低声音,“‘洗冤录第三十七页,需配防风三钱’。”这是她与李承恩的暗号,第三十七页记着锁心草的解药,防风是关键药材,暗指“急事相求”。
周县令的眼神变了变,侧身让她进了巷弄深处:“跟我来。”
周县令的家就在巷尾,是座不大的宅院,院里种着几株桂树,正开得热闹。进了书房,他屏退下人,才开口:“姑娘从京城来?”
“是。”
“怎么称呼?”
“左忆”
左忆从背篓里取出张纸,上面画着断魂草的样子,“周大人可知这草?”
周县令看着图纸,眉头紧锁:“断魂草?剧毒之物,怎么了?”
“京城西郊外近来出现不少,有人故意培育,已害了数人。”左忆简明扼要地说,“培育者是三皇子李珩的人,腰间挂着老虎玉牌。”
周县令的脸色沉了下来:“三皇子?他被禁足期间,竟还敢在宫外动手脚?”
“他怕是想借毒草制造恐慌,再嫁祸他人。”左忆想起那些中毒的农户,“若不尽快处理,恐生大乱。”
周县令在书房里踱了几步,忽然停下:“姑娘可有证据?”
“有个叫赵二的菜农见过那太监埋草籽,可作证。”左忆顿了顿,“只是……我不便露面,还请大人派人去京城城西一带查访。”
周县令点了点头:“我明日就派亲信去。只是……”他看着左忆,“此事牵扯皇子,需禀报太子殿下定夺。姑娘可否在此等候几日?”
左忆知道这是应有之义,点了点头:“我在客栈等消息。”
离开周宅时,桂花香浸了满身。左忆望着青州城的夜空,星星比京城亮得多,心里却沉甸甸的——她不知道李承恩会如何处置,更不知道这会不会再次将自己卷入漩涡。
接下来的几日,左忆在青州城闲逛,帮药铺里的老掌柜整理药材,日子倒也平静。直到第四日傍晚,周县令的亲信匆匆找到她,递来封信。
信封上是李承恩的字迹,只有一行字:“已收网,速归京,需你指证。”
左忆的心猛地一沉。归京?指证?她终究还是躲不过。
她问亲信:“周大人怎么说?”
“大人说,殿下已有安排,姑娘只需跟着小人走便是。”亲信的语气很恭敬,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
左忆握紧信纸,指节泛白。她知道,这是命令,不是商量。李承恩需要她这个“证人”,将李珩的罪证坐实,彻底断绝他翻身的可能。
当晚,左忆跟着亲信登上一辆不起眼的马车。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规律的声响,像在倒数回京城的日子。
她掀开窗帘,最后看了眼青州的夜色。桂花香还萦绕在鼻尖,却已恍如隔世。
回京城的路走得很快,马车日夜兼程,只用了三日。进了城,左忆没被带去东宫,而是住进了城郊的一座别院,院外守着侍卫,名为保护,实为软禁。
“殿下说,等时机到了,自会来见左姑娘。”侍卫把她领到客房,语气平淡。
客房收拾得干净,桌上摆着她惯用的药碾和银针,甚至还有本新的《洗冤录》。左忆看着这些,忽然觉得荒谬——李承恩连她的习惯都摸透了,这掌控欲,比太后更甚。
她在别院住了五日。这五日里,京城暗流涌动。
先是城西乱葬岗附近挖出大量断魂草幼苗,证实是人工培育;接着,那个挂着老虎玉牌的太监被抓,严刑拷打下招认是受李珩指使;最后,御史台联名上奏,弹劾李珩“私植毒草,谋害百姓”,请求陛下严惩。
一切都按李承恩的剧本上演,只等她这个“关键证人”出场,给李珩最后一击。
第六日清晨,李承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