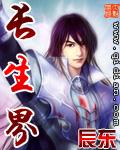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许君长乐loft > 乱世评下(第1页)
乱世评下(第1页)
明堂素有旧规,铜铃声响,意味着有人花了银子,花钱者可提一问,让众人为之一议。
“噤声。”明堂主事之人朗声道。
随着铃响声毕,一名小厮捧着竹盘缓缓从高座的雅间后走出,竹盘之上,放着一枚明晃晃的金锭,金锭压着的,便是那雅间中的人想问之事。
“我们家老爷有问,明堂之中若有能答者,这便是赏金。”
主事走上前去,眼神落在那一枚金锭之上,轻轻拿起一看,底下烙着官印,说明这座上之人,若非公卿,便是王室,他静静地放下那枚金锭,拾取盘中的竹笺,定睛一看,上面所问之言,更是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所问何事啊?”众人之中,有人见主事久久不言,不免好奇地问道。
主事看了一眼小厮,轻声问道:“可否问一句尊驾姓氏?”
小厮淡淡道:“不是什么大姓。”
主事见他不想回答,便也不敢多问,只是这竹笺捧在手心,就像烫手山芋似的,扔也不是,放也不行。
小厮见主事犹豫,进而又道:“听闻明堂评议,不避权贵,不讳天家,怎么?这等民间小谈,却不敢议了?”
主事顿了顿,旋即转身,冲着众人朗声念道竹笺上的字:“此问是,帝乃天帝,非人主之号乎?”
众人皆是一怔,刚才还窃窃私语的堂下,瞬间哑然一片。
这一问,问的是当下最荒唐,却又最敏感的话题。
如今天下四分,北朔刘帝以其君权受命于天自称为帝,但国力能与之相抗衡的南疆却因崇尚天神,认为凡人之躯不可僭越帝称,南疆国主只称王而不称帝。西伥草原蛮子各自占地为王,好几个政权都算不上统一,零零碎碎的王有好几个,自然也无人称帝。
东袭作为四个政权中,国力不算强,但位置却最尴尬的那一个,依然保留了祖上留下来的帝称,又恰巧挤在北朔和南疆的中间,显得十分尴尬。于是,民间便有了如此荒诞自颓的言论。
可这毕竟是民间小谈,不登大雅之堂,更不会有人敢将其拎到台面上来评议,国之帝皇,因为惧他国之威势,便去帝称王,那与亡国有何区别?
一时之间,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明堂之中,竟无一人敢随意开腔。
半晌后,雅间中的小厮又出来了,在原本的金锭子边上,又放了一枚,见还是无人说话,便一枚又一枚的加,放到第五枚的时候,人群中开始有了细碎的讨论声。
毕竟这明晃晃的五枚金锭子,都可以在绥京城郊买上一套小院了。
“此言非也。”堂下一位年轻儒生喊道,“帝号乃祖宗之法,乃大袭山川所认,若无圣祖,便无大袭,帝号不存,国将不国。”
他身下另外几个学子也跟着应和道:“是啊,帝号不存,国将不国啊。”
小厮顿了顿,回了雅间,片刻后又出来了,站回了原位上,继续往那竹盘上放金锭子:“我家老爷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答话。”
眼见着竹盘上的“京郊小别院”,一锭一锭地变成了“城中大庭院”,堂下的才子们更是按捺不住了。
反正只是评议,又并非真的要圣上去除帝号,寒门学子们本就一无所有,搏一搏说不定就能少奋斗大半辈子。
终于,刚才吵得最凶的那番辩论中,那个被称作文德兄的人忽而开口了:“雅间中的贵人,出手如此阔绰,真的只是想听我等说一句肺腑之言吗?”
小厮传话道:“公子但说无妨,今日之言,仅留于堂上。”
“好。”这位文德兄冲着雅间的方向微微作揖后,不疾不徐道,“鄙人认为,此言虽偏激,却不无道理。战国时,魏国与齐国互称王号,联手抗秦,而秦为了拉拢魏国,尊魏王为西帝,魏王为避此锋芒,主动去除帝号,后与诸侯联手抗秦,秦王见势不妙,随即也取消了帝号,以退为进,看似妥协,实则却是审时度势的权宜之策。”
他话音刚落,楼上就突然炸响一声怒喝:“胡扯!”
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那高声之处,只见二楼的雅座之上,帷帘后腾地站起一位精壮的少年人,他朗声嚷道:“这种话都说得出口,我看你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学子,而是北国来的细作!”
“阿升。”张岁安眉头微蹙,连忙给江崇的随从递了个眼色,“还不快让你家公子坐下。”
可阿升哪敢啊,最多是扯了扯江崇的衣角,小声劝道:“公子啊,张家公子让你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