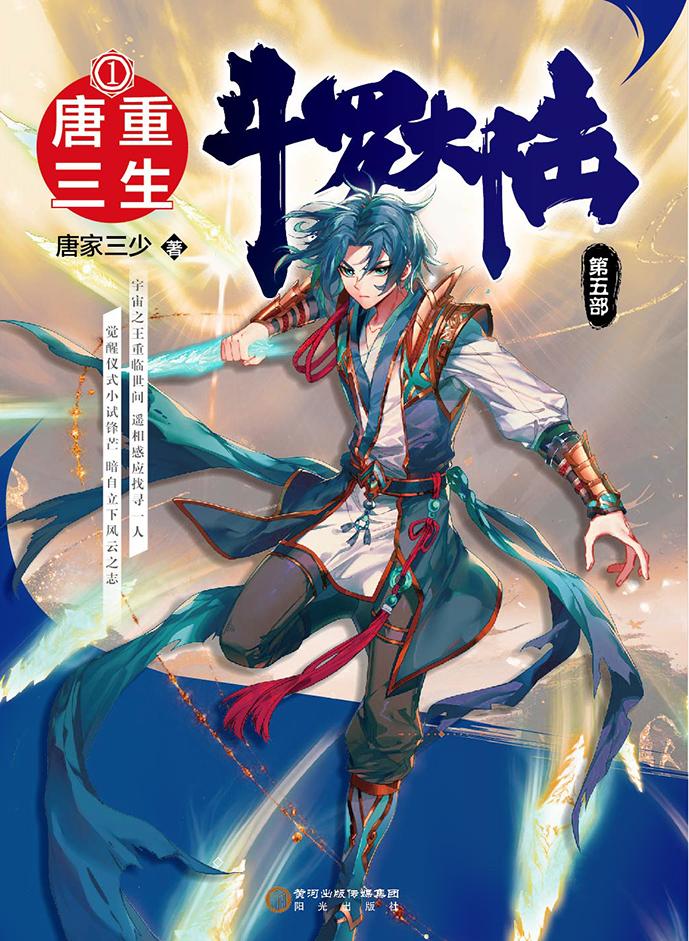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龙傲天他不想说话 > 第 4 章(第3页)
第 4 章(第3页)
谢世安听不得这话,瞪眼道:“可我是男子!”
江湖郎中笑道:“岂非没有女中乾元。”
谢世安迟疑了下,似乎真思索了片刻,最后还是恪守本心道:“不成,雌伏于人下之事,实不能也。”
谢世安又敷衍应付两句,当着他面,又塞了两颗秘药。
江湖郎中摇摇头,无奈谈了口气道:“也罢也罢。”
按照惯例,走前,他给谢世安把了一下脉,确认下药效如何。
指腹搭在谢世安腕处,未几,他突然惊讶道:“你遇上乾元了?”
谢世安道:“未曾,怎么?”
江湖郎中:“你这脉象,体内信香同前几次相比,要平稳不少,似是有过纾解……那或是有过欢爱之事?”
谢世安想到昨日之事,不自在的咳嗽两声道:“确有其事。”
江湖郎中扬眉,多看了他两眼,放下了点心道:“也好,虽说不如乾元信香……”
谢世安扬眉:“你这意思是,做这种事还可以当秘药用?”
江湖郎中:“非也,只是能稍缓,而且这房中之事,能生人,能煞人。譬如水火,知用之者可以养生,不能用之者立死矣。*”
什么叽里呱啦乱七八糟的。
谢世安心道:那下次情期,岂不是还可以找李承稷帮忙?既能促进兄弟情,还能缓解情期。
爽哉。
这江湖郎中看谢世安没心没肺那样,便知没有把他话挂心,走前瞧着谢世安腰间挂着枚羊脂白玉佩小金坠,旁边桌案上丢着芬芬馥郁的瑞脑承露金粟囊,床榻上甚至还挂着条多看两眼,都能掉脑袋的朱里朱绦鞶革。江湖郎中摇了摇头,只喃喃道:“生得一副谪仙堕尘的玉貌,更兼坤泽之身,才貌双绝,若是稍通情丝,便是那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可惜偏生一根筋,墨守成规,榆木疙瘩。”
江湖郎中长叹:“奇人,真个奇人也。就这般性情,日后免不了多生事端。”
是药三分毒,这秘药服下虽能极快缓解情期,但会让人冒虚汗,犯困,信香短暂难抑。
前者都还好,也就最后那信香容易坏事,不过谢世安没在意,他身边几人都是中庸,这影响,约等于无。
谢世安在去书院路上,心里头总时不时想起昨夜同李承稷在汤殿之事,一个劲念叨:没事没事都是大男人的什么没见过互相帮助一下有什么他不问我不说他一问我惊讶……
思绪神游,游廊转角蹲着个人,他都没注意上。
险些一脚蹬人屁-股上。
打眼一看,这蹲墙角的竟是他胞弟谢既白。
“蹲门如犬,非盗即娼,谢既白,你是强盗还是男娼。”谢世安倚在一旁,双手环胸,对谢既白道。
谢既白撇撇嘴,拍了拍屁-股起身委屈道:“哥,我看你没把我当弟,也没把我当人。哪有这么说弟弟的。”
谢世安呵呵道:“怎,强盗男娼不是人?”
谢既白眼球一转,狡邪一笑,扭着腰往谢世安身边挤说:“也行,那我便是哥哥的小男娼。”
只是这话音刚落,他嘴角的笑意倏地一凝,视线凉凉的落在谢世安的后颈。
谢世安浑然未觉他眼神不对,被谢既白那一通话恶心的一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骂了句“滚蛋”,脚底抹油,一袭绛朱色外袍被脚风带着翻飞,恨不得离他这个变-态弟弟越远越好。
谢既白就站在那处,静静看着谢世安逐渐匿去的背影,眯眼,冷笑了声:“哥哥的信香真好闻呢,可惜了,混了道好臭的乾元信香。”
“叫人火大。”
李承稷照常是来的最早的那个。
谢世安远远就瞧见他拿着书卷,端端正正坐窗边。
配得上那诗里“闲窗展卷无语,风入松筠自清”的儒雅模样。
先前那点不自然,在被谢既白恶心一通后,瞬间通透了。都是兄弟,他和李承稷玩的,还没他谢既白一句话来的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