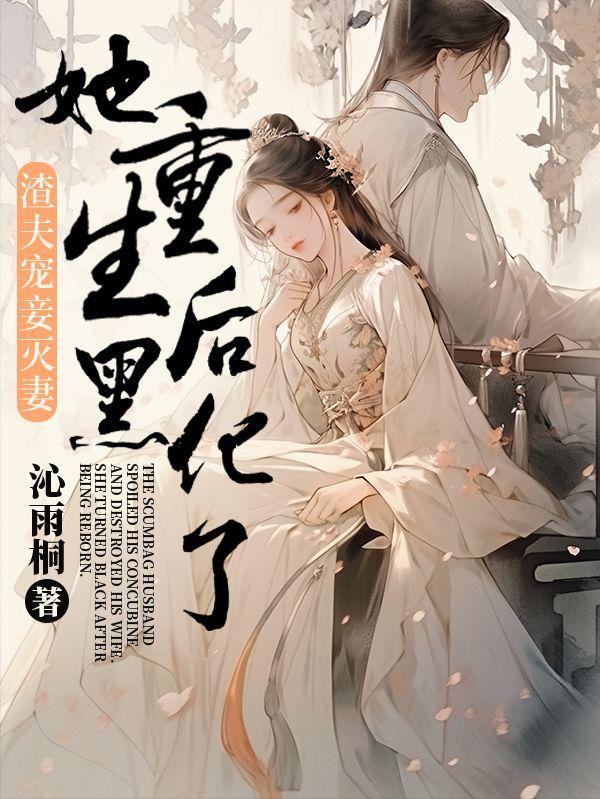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簪缨世族by缓归矣TXT > 第60章(第2页)
第60章(第2页)
崔述站直身子,目光中闪过一丝犀利,又归于平静:“我已非崔氏族人,当不起‘内兄’二字。无非是以学生之身来见业师,薛司使允否?”
薛向微抬下巴,长随请崔述往东:“崔少师请随小人来。”
缉狱司并非新辟之所,乃肃政司搬迁后遗留下的旧地,就在出景运门往东两里,离皇城极近,听上令行事甚为方便。
监狱亦是当年所遗留,占地不广,条件亦不好,但胜在来往其间的都是朝中官员,收拾得还算清爽,闲置多年,仓促启用,也不致一片狼藉。
杜悯被押在里间,单独的一间牢狱。
崔述走近时,最先落入眼帘的是一张木床、一张书案乃至一张榻上小几。
狱卒开锁离去,崔述迟疑着踏入其间。
杜悯睁开虚眯着的眼,长叹了一口气:“该说的话都说尽了,你本没必要来。”
崔述躬身行礼:“违逆师命,还请老师责罚。”
杜悯伸手虚扶他一下:“坐吧。身在此间,还拘泥什么礼节。”
崔述挨着榻沿坐了,触感柔软,不觉硌人。
“这大半月闲来无事,我将《倦翁笔记》的末卷写完了。先前拖了许久都难以下笔,许是知大限将至,这几日倒文思泉涌行云流水起来,一卷竟无一字涂改。你若还能静得下心,也来读读这一卷。”
“老师,思虑至今日,当认我也非完人,无法坐视此事发生。”
“待我去后,帮我整理此籍,定稿后付梓印书,天下士人若有几人能传我之道,此生亦慰矣。”杜悯转了话头,但话说到一半,却倏然一顿,“罢了,德行有亏,不配传书于世。”
“此书历六载春秋方成,无论如何,我都会整理面世。词句章格见真心,配与不配,当留世人来评。”崔述眸中晦暗,道,“但当老师亲眼见证为宜。”
杜悯没接他的话,将几上的笔墨收至一侧书案上,转而道:“替我刻方闲章吧,往年你总要刻几枚印信给我,往后应当没机会了。”
几上印石、刻刀、砺石等一应俱全。
崔述执起这方玉石,右手握着凿刀,却分毫动作也无。
杜悯也不说话,只眼含着笑看他。
半晌,崔述终于开了口:“老师想刻个什么章?”
杜悯捻着长须,思虑一阵后,方眯着眼道:“永昌新政历时不到四载,却倾我前半生心血。这本《倦翁笔记》,则耗尽我后半生肝胆。我知你言出必行,我去之后,也无法阻止你将此书刊印面世。但身负罪愆,往后不得以我之名将此书付梓,污无辜笔墨,便以此未公之于众的私号行世罢。”
“是。”崔述垂首,将油纸奉上,“请老师赐笔墨。”
杜悯站起身来,执笔蘸墨,迅疾下笔,一气呵成。
崔述取白芨水涂于印面,覆油纸于其上,用笔杆徐徐碾压,以使墨迹反渗。
待将油纸揭下,反文拓于玉面,他执刻刀慢慢雕刻起来。
狱中寂静,只有刻刀之声响响停停。
刀过之处,玉屑簌簌。
杜悯看了半晌,说起一事:“那时京郊税案,你锒铛入狱,我没有去看你。”
刻刀顿了一下,声响停了半息,又重新响起来。
“老师那两月在京郊玄都观讲学,为听您讲儒,多少外地士子远道而来,耗资甚巨,老师自不能半途而废。”
“但你出京那日,讲学已毕,我去了。”杜悯叹了一声,“在九里亭,看见徐子衍去送你,那时想着,即便为师不能再送你一程,但总有人能送你行得更远,便没有现身。”
刻刀忽地错了位,食指伤了一道极深的口,汨汨往外淌着血。
“人和人之缘分,总是只有一程。与背负生养之恩的父母尚且如此,与老师又岂会有所不同?述安,老师只有两载便至古稀之龄了,已是高寿,与你之缘分,便只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