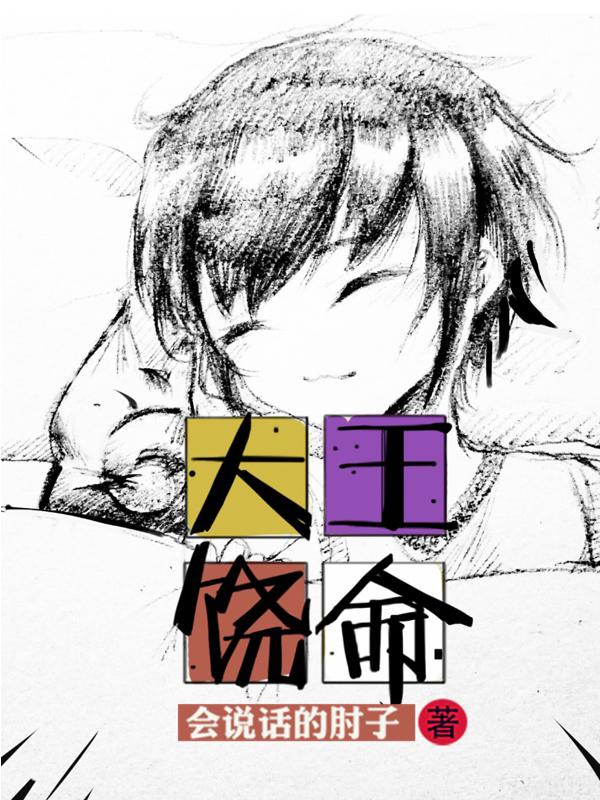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错位关系1∨1方糖陆岩127 > 补课风波(第1页)
补课风波(第1页)
月考成绩在周一贴了出来,毫无悬念。江叙的名字高悬在年级红榜首位,总分拉开第二名一大截,尤其是数理化,几乎满分。他的名字在课间被频繁提及,伴随着“学神”、“非人类”之类的低语和惊叹。他本人却对此毫无反应,仿佛那榜单上的名字与他无关,依旧按自己的节奏看书、做题、去图书馆。
江昭的成绩则在中下游徘徊,数学和物理果然如他所料不太理想,但语文和历史居然还过得去,体育成绩更是毫无意外地满分。他对着成绩单咂咂嘴,哀嚎了两声“完了回家要挨揍”,转头就被队友勾着脖子拉去讨论下午的班级篮球赛了,那点沮丧来得快去的也快,像秋日里一阵无关痛痒的风。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家庭内部。
成绩单需要家长签字。晚饭后,江昭磨磨蹭蹭地拿出那张纸,递给了江叔叔。江叔叔看着上面的分数和排名,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但语气还算温和:“小昭,这个成绩……不太行啊。高中不比初中,得加把劲了。”
母亲在一旁打着圆场:“刚开学嘛,还没适应,下次努力就好。小叙成绩好,让他多帮帮弟弟。”她说着,充满期待地看向江叙。
江叙正低头喝汤,闻言动作顿了一下,没应声。
江昭挠挠头,嘿嘿笑了两声:“爸,阿姨,我知道啦!下次一定考好!哥他学习忙,我自己能行!”他试图蒙混过关。
江叔叔却没轻易放过,他放下成绩单,看向江叙,语气变得郑重了些:“小叙,你学习上有方法,成绩也好。以后多带带弟弟,监督他一下,行吗?你们兄弟俩在一起,也方便。”
这话带着不容拒绝的意味。母亲也在一旁连连点头。
江叙抬起眼,目光平静地扫过江昭——后者正冲他挤眉弄眼,一副“千万别答应”的哀求表情——然后对上江叔叔期待的目光。他沉默了几秒,才淡淡地开口:“看他自己的意愿。我不会强迫。”
这回答模棱两可,既没答应也没拒绝。江叔叔似乎还算满意,点了点头:“嗯,小昭,多跟你哥学学!”
江昭松了口气,赶紧把成绩单收起来,埋头猛扒饭,不敢再多说一句。
然而,家长的干预往往比当事人的意愿更有力。从那天起,江昭被迫开始了“课后辅导”时间。
起初只是象征性的。江昭会极不情愿地拿着作业本蹭到江叙书桌旁,装模作样地写几分钟,然后就开始走神、玩笔、或者试图找江叙聊天。江叙从不主动催促,只是在他问题目时言简意赅地解答,在他明显走神时用笔敲敲桌面,或者干脆不理他。
江昭耐性极差,往往坚持不到半小时就抓耳挠腮,找各种借口溜走:“哥我渴了去倒水”、“哥我肚子疼”、“哥我好像听到手机响了”……江叙从不阻拦,随他去。几次之后,江叔叔察觉了,严肃地批评了江昭,并要求江叙“严格一点”。
于是,辅导变得正式起来。每晚八点到九点,被固定为“学习时间”。江昭必须待在江叙房间里,完成当天的作业和额外的练习题。
这一个小时,对两人都是一种煎熬。
江叙习惯了绝对的安静和高效,江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干扰。他呼吸的声音,翻书的哗啦声,写字的沙沙声,偶尔烦躁的叹气声,甚至只是坐在那里散发出的那种坐立不安的气场,都让江叙难以完全集中精神。他发现自己需要花费更多的心力才能屏蔽掉这些干扰。
而对江昭来说,这简直是无期徒刑。被按在书桌前,面对枯燥的公式和单词,旁边还坐着个冰山一样、气压极低的“监工”,他浑身像长了刺一样难受。他会不停地变换坐姿,腿在桌子底下无意识地抖动,笔帽咬了又咬。
“安静点。”江叙第三次出声提醒,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
江昭猛地停下抖动的腿,垮着脸:“哥,我真的学不进去……这英语单词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
“那就看到认识为止。”江叙头也不抬,笔下不停。
“这比跑一万米还累……”江昭小声嘟囔,认命地继续瞪着单词表,眼神发直。
有时,江叙会给他讲题。他讲题极其精炼,步骤清晰,但没有多余的废话和鼓励。江昭往往需要全神贯注才能跟上他的思路,稍微一分心就会漏掉关键。
“等等哥,这里为什么用这个公式?”“定义。”“那这个数怎么带进去就变了?”“计算。”
江昭常常被这种简洁到近乎冷酷的回答噎得说不出话,但又不得不承认,江叙的方法往往是最直接有效的。
偶尔,江昭也能灵光一现,迅速理解一道难题。这时他会忍不住露出得意的表情,甚至想和江叙击个掌庆祝,但每次对上江叙那双平静无波、仿佛在说“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的眼睛,那点兴奋就又缩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