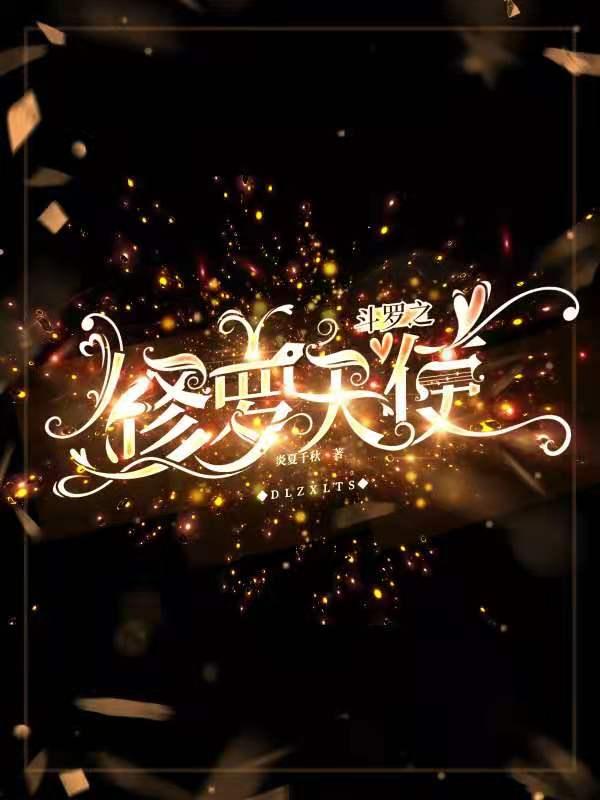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错位关系1∨1方糖陆岩127 > 旅游(第1页)
旅游(第1页)
高考结束后的日子,像突然松开了发条的玩具,一下子失去了紧张急促的节奏,变得慵懒而漫长。阳光变得格外慷慨,毫不吝啬地洒满每一个角落,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叫,宣告着盛夏的正式来临。
最初的狂喜和宣泄过后,是一种巨大的、几乎让人无所适从的空闲。不用再早起背书,不用再熬夜刷题,不用再对着倒计时数字焦虑。时间仿佛一下子多了出来,流淌得缓慢而惬意。
江昭和江叙花了整整两天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几乎什么都没干,只是瘫在沙发上,或者并排躺在江昭房间的地板上,听着风扇嗡嗡转动的声音,看着天花板发呆,享受这种大脑彻底放空的奢侈。
父母似乎也默许了这种“报复性”放松,没有过多干涉。
到了第三天,那种无所事事的空虚感开始被另一种蠢蠢欲动的期待所取代。
江昭一个鲤鱼打挺从地板上坐起来,眼睛发亮地看着旁边还在神游的江叙:“哥!我们是不是该计划一下……旅游的事了?”
看海。这个在无数个疲惫夜晚被反复提及、用以熬过艰难时光的约定,终于被摆上了日程。
江叙的眼睛也瞬间亮了起来,他坐起身,重重地点了点头:“嗯!”
接下来的几天,书房里的复习资料被彻底清理干净,取而代之的是摊开在书桌上的地图、旅游攻略和亮着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两人头碰头地挤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目的地、行程、预算。
“去青岛怎么样?听说那边海水挺蓝,而且有老建筑,可以逛逛。”“或者厦门?鼓浪屿好像很浪漫。”“三亚呢?阳光沙滩!就是预算可能有点超……”“要不去近点的?北戴河?……”
每一个地名都代表着一种不同的诱惑和想象。争论、比较、计算,这个过程本身都充满了乐趣。他们像两个第一次独立规划世界的孩子,充满了新奇和兴奋。
最终,经过反复权衡(主要是预算和时间的权衡),他们选定了一个距离适中、消费也不算太高的沿海城市。订车票,查酒店,做攻略,每一个步骤都两人一起商量决定。
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母亲会偶尔过来,送点水果,状似无意地瞥一眼电脑屏幕,然后委婉地提醒:“出去玩儿注意安全啊,海边风大,别贪凉。”甚至有一天,她默默地把一盒崭新的防晒霜和一瓶清凉油放到了书桌上。
父亲则依旧沉默,但在晚饭时,会罕见地问一句:“钱够不够?”虽然语气还是硬邦邦的,但那份笨拙的关切,两人都清晰地感受到了。
这种变化让江昭和江叙心里都暖暖的。他们知道,坚冰正在加速融化。
出发的前一晚,两人都有些兴奋得睡不着。行李早就收拾好放在墙角。江昭又溜进了江叙的房间,两人并肩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毫无睡意。
“明天早上七点的车,会不会起不来?”江叙有些担心地问。“放心,我设了三个闹钟!”江昭信心满满,翻过身,侧躺着看着江叙,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光,“哥,你兴奋不?”“嗯。”江叙老实承认,嘴角忍不住上扬。“我都想好了,”江昭的声音带着憧憬,“我们要去踩沙滩,捡贝壳,早上要看日出,晚上……晚上要去吃海鲜大排档!还要……”他絮絮叨叨地说着计划,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期待。
江叙安静地听着,心里也被那份快乐填满。他伸出手,在黑暗中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江昭的手,与他十指紧扣。“嗯,都去。”他轻声应和着。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两人就轻手轻脚地起床了。父母卧室的门还关着。他们洗漱完毕,拎起行李,正准备悄悄出门,母亲卧室的门却开了。
母亲穿着睡衣走出来,眼里还有睡意,却坚持要送他们到门口:“路上一定小心,看好东西,到了给家里打个电话……”“知道了妈,放心吧。”两人连连点头。
就在他们换好鞋,准备开门时,父亲卧室的门也开了。父亲站在门口,沉默地看着他们,然后走了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折得整整齐齐的钞票,塞进江昭手里。“……拿着,穷家富路。”他说完,不等两人反应,就转身回了房间,关上了门。
江昭捏着那还带着父亲体温的钞票,愣在原地。江叙的眼眶也有些发热。母亲叹了口气,拍了拍他们的胳膊:“你爸他……就是嘴硬。快走吧,别误了车。”
走出楼道,清晨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两人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感动和一种更加坚定的东西。
火车站人流如织。挤上列车,找到靠窗的座位放好行李,当列车缓缓启动,熟悉的城市风景开始向后移动时,一种混合着离家的怅惘和奔向自由的兴奋感,强烈地冲击着两人。
江昭兴奋地指着窗外的景物,喋喋不休。江叙则安静地看着窗外,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
列车加速,城市渐渐被抛在身后,视野变得开阔,绿色的田野和远山映入眼帘。
江昭渐渐安静下来,他转过头,看着江叙被窗外阳光镀上一层金边的侧脸,忽然低声说:“哥,就我们两个了。”
真正的、完全属于他们的旅程,开始了。
江叙回过头,对上他亮晶晶的、盛满了笑意和爱意的眼睛,也笑了起来,主动伸出手,握住了他放在腿上的手。“嗯。”
列车呼啸着,载着两颗年轻而雀跃的心,奔向蔚蓝的大海,也奔向他们独立规划的第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阳光洒满车厢,也照亮了他们紧握的双手和眼底璀璨的光。这个夏天,注定会因为这场旅行而变得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