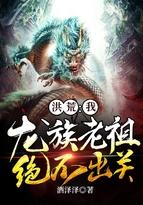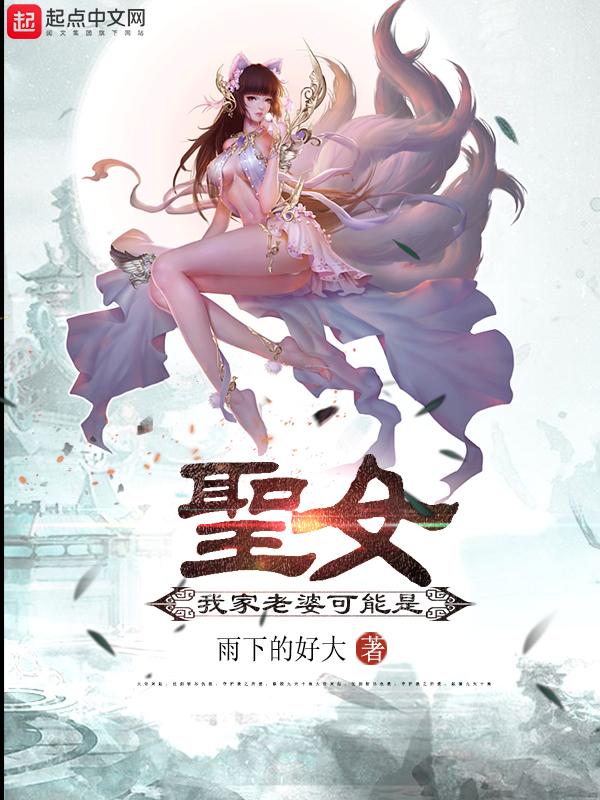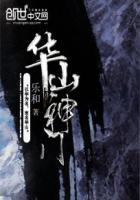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作者蓝烬 > 第64章(第2页)
第64章(第2页)
“主席,教育是个天大的问题啊,我现在只能是提出一个轮廓。城区和乡寨应该尽量建立起幼儿园体系,将劳动力从养儿育女中解放出来,并做好幼小衔接。”
“接下来建立起小学6年、初中3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这是必须列入法律的强制性教育,所有父母都必须遵循,让所有儿童能完成初中文化水平的基础教育。在初等教育领域,将数理化、语文政治、自然生活和基础军事,作为教育基础,其它的暂不涉及。尤其是什么外语教育,莫名其妙,我们需要那么多懂外语的人吗?浪费这些时间,不如集中到更适合的主课上。高中生开始学习英语,就足够了,要好好学习外语,主要还是在大学里。”
“接下来对初中毕业生,我有一个比较疯狂的想法。”
主席的兴趣提高了:“疯狂?你这描述,说明不简单,那说来听听。”
李思华说出她不同于常规教育思考的方向:
“我觉得,最擅长学习的30%上高中;10%去专业性的技术学校和中专;25%加入流动性民兵组织;其余35%,本地就业,补充本地劳动力。”
“我认为,以大学为目标的高中生,有25%的青少年,已经足够,否则会产生“过度教育”的问题,多数人继续学习的,并不是生活需要的本领,而是过多的他们未来用不上的知识。”
“从我前世的经验看,最顶尖的研发人员,日本的比例大概是0。65%,即1。2亿多人口中,有70多万的研发人员,已经是最高的比例;美国的比例大概是0。5%,3。3亿人口中有160多万研发人员;欧盟的比例还低于0。5%,近6亿人口中有230多万研发人员。如果我国未来能达到日本的水平,这个数字就很高了,要是有20亿人口,就意味着1300万研发人员,会超过全球其它国家研发人员的总和。”
“制造业即工业人口中,除了战争期间,制造业的巅峰大约也就是15%的人口,其中假设工程师的比例高达20%,那也就是总人口的3%,加上一些储备和初级补充的技术人员,包括研发人员在内,占到人口比例的5%,已经是不得了的高度了。”
“所以去掉科技和制造业,其它需要高级文化知识的,即企业白领和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很多社会组织,教师等等,按照前世各国的基本情况,能占到总人口的10%,也已经是很高的水平。”
“综合来看,如果不浪费的话,每年人口比例的15%上大学,已经足够,不过为了保险,我们把这个数字,放到20%的比例。预计建国初期,每年新生人口,大约会是1500万左右,即很可能一段时间后,每年会培养300万的大学生,这个数字肯定是足够的。”
“我曾经向您描述过前世的大扩招,一年上千万大学生,我始终觉得这是资源错配,大学教育质量是明显下降的,所谓大学生,其实已经名不符实。”
“如果将高中生的比例设定为30%,就是要在高中形成竞争的学习气氛,因为会有13的人被淘汰,只有自己优秀,才能保证上大学。淘汰下来的10%,要根据他们的意愿,总的原则,大约是5%补充入流动民兵组织,使得这一组织吸纳青年的比例,实际上不是25%而是30%。其余的5%,就当地就业。”
“这样的话,未来干部的来源,就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学生及更高教育水平的革命知识分子;第二部分是流动民兵组织培养出来的相当于大专文化水平基层干部。”
“我非常重视流动民兵组织,它是大学之外的另一个巨大的教育体系,是工作、革命实践与知识、能力教育配套的体系。这个体系比起大学来更加庞大,也更加复杂,因为它不是象牙塔,而是青年与社会接轨的中介组织。”
对于这个流动民兵组织的设想,是主席对李思华教育体系思想中最重视的部分。他认真地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们既然要避免严厉的人口节育,反而必须用好庞大的人口规模。”
李思华还与主席讨论了全社会的的“终生教育”体系,她认为这方面要建立两层体系:
“第一层是大学与企业合作的,各产业领域的科学技术进阶培训学校,由专业人员兼职或专职上课,讲述产业领域科技、产品、工艺、材料等方面的最新发展,让产业领域中的技术人员,能够不断进步。”
“第二层是非科技领域的教育培训系统,例如政府和企业的所有机构,都必须设有培训部门,对于工作人员,不断进行国家新的方针、政策、理论的培训,进行工作领域涉及的案例、社会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培训和考核。企业则同样应该保持不断的职业培训和教育。”
“通过教育体系,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学习型社会,活到老,学到老,不能让人民在本身低落的知识水准上躺平,必须强制性地、诱导性地让他们不断进阶。”
李思华认为,教育体系直接影响到就业。就业除了受到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以外,也和教育的结构是否适合就业息息相关。她沉重地对主席说:
“教育结构的重点之一就是考虑就业的问题。就业,是让所有国家头疼的头等大事,而且是与未来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趋势矛盾和相冲的。”
“从长期看,一个可怕的趋势是,几乎所有的职业,需要的工作人口数量,都在不断减少。科技发展创造的新就业机会比较少,而且要求很高;而旧产业衰退或者技术进步淘汰下来的人更多,这就造成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的比例,是只好到简单的社会服务业就职,即城市中所谓的低端就业,例如送快递、餐厅服务等等,这些低端就业,本身就很容易会被下一步的科技进步,例如无人化和智能化所替代。”
“我前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时,一个鞋厂,可能会用几万人来生产鞋子,等到2020年,也许这个鞋厂只剩下一两千人,但产量反而是几十年前的十倍。这样的故事,到处都在发生。为什么到后来各国都有大批量的青年倾向于躺平?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无可奈何了嘛,如果自己去找工作,就只有这些城市的低端就业,永远看不到出头之日。”
“我们在最近的几十年,还不用太担心,制造业还在蓬勃发展,尤其我国的大建设,要改天换地,有无数的基建工程,城建工程、乡寨的发展工程。但是未来总有一天,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窘境,教育结构是百年大计,需要早早地为此做好准备。”
“单个行业的就业需求减少,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不是我李思华,甚至不是我党,可以扭转的。我们也不能因此保护落后,排斥进步,那最后会让国家和民族倒霉的。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呢?”
“第一、就是让教育贴近社会的就业需求,如果教育出来的人,根本不适合社会的工作需要,失业就会更严重,而社会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经济不好,就业就更糟。”
“第二、就是努力实现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如果经济一直在增长,至少就业还能得到一定的保障,社会对就业的需求,在一些方面萎缩了,但在一些新的方面,还在增长,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就业压力。”
“第三、就是预设退路,准备好一些能大规模接受就业人口的手段。例如乡寨,除了是为了改变我国农村的基本生态,实现现代化和革命化以外,很重要的一个预想,就是作为就业的退路。”
“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有生活困难,或者是对低端的工作不满意,那么可以去乡寨,3亩地一栋房,生活压力不大,对于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配套的一个手段,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发展到50%的程度就差不多了,需要管控,不能再让城市的总体人口比例,无限制地增加下去,等到发展到西方那样80%以上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就算没有明显的贫民窟,但新贫阶级的存在,是必然的、肯定的。”
“考虑一些其它策略,一些长期性的超级大工程,也是大规模吸纳就业人口的方法。例如未来我们在国力承受得起的前提下,诸如藏水入疆、黄河治理、大西北环境改造等的超级大工程,将国家收入的一部分转移支付,组织起大量潜在的失业人员,投身于国家万里山河的改造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很多人就可以不但获得工作,而且创造了新的生活环境、新的城市和乡寨,获得了永久的事业。”
“当然,这些超级大工程,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不过,我们对于生态环境的态度,不是保持原始荒漠,那有什么意义?我们的态度是提升和改进,让绿色森林,进展到国土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