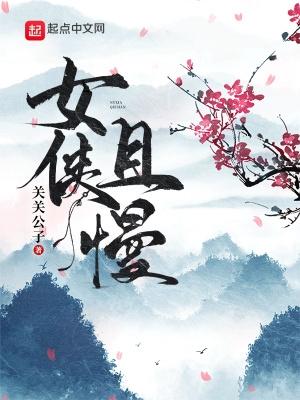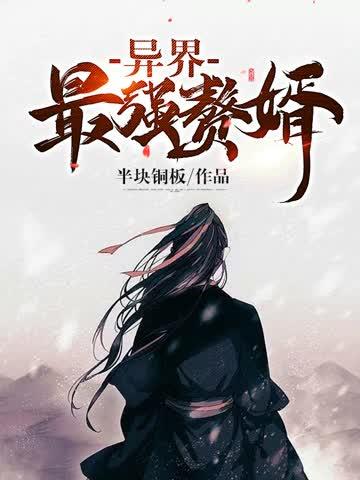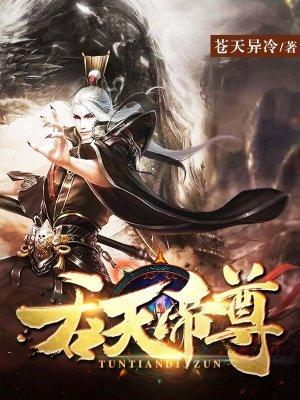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作者蓝烬 > 第65章(第3页)
第65章(第3页)
主席诧异地笑了:“你一个军官,都读到博士了,还买不起房?”
李思华感慨地回答:“我读的学校就是在重庆,读博士的时候已经差不多30岁了,我挺喜欢重庆的,想着要是以后退役了,最好有套房子,所以那个时候有点想买房,可是2020年的重庆市区,我一个普通军官,哪里买得起呢?当然如果在偏远的郊区,咬咬牙还是能付得起首付,不过自己觉得没意思,就算了。反正是军人,跟着部队走,总有宿舍住。”
主席的神色变得有点严峻:“你一个校级军官,都买不起房,这个房价,确实是很贵了。”
李思华点点头:“所以在这个时空,我们不应该重蹈覆辙。整体来看,教育培训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前世拆了这个行业,号称有1400万人失业,但毕竟也撑下来了。所以提前的法律法规,就可以预防这个问题。”
“比较头疼的是房地产和医疗问题。”
“在这个时空不要说很远的未来,单单预计到1965年~1970年,我国的人口就可能超过10亿,假设届时的城市人口是4亿,那么至少就是1亿个家庭以上。如果全部是政府建筑房屋,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担得起。政府能建成一部分廉租房之类的过渡房屋,提供给新入城市者临时居住,就已经不错了。”
“城市不是乡寨,乡寨以平房为主,土地、木材、打基础的成本都很低,主要成本就是水泥,就连人工都由合作社依靠互助解决了。所以建房的难度很小,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但城市就完全两样了。”
“在城市,一个根本的原则是,我们要不要通过控制土地的价格,来为地方政府提供一部分的资本?我认为,政府通过房地产来获得资本,是必然的,否则地方财政不足,但是通过抬高地价的方法,则不可取。”
“从国际的经验来看,前世国家选择类似香港的房地产政策,从“居者有其屋”的角度看,这个模式是远远不如新加坡的“组屋”模式的。可是为什么还是用香港模式呢?一言以概之,因为缺乏资本。”
“新加坡是个非常小的城市国家,所以自筹资本,以建屋局的模式,政府来修筑绝大部分的房屋,是做得到的,然后再将之出售给居民。相应的,我原时空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开发房地产的时代,国家是缺乏资本的,而且在大部分行业市场化了以后,建筑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因此不可能按照新加坡的模式。”
“但在我们的时空,资本的问题有所改善。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主要参考新加坡组屋模式。”
“我的设想是,中央设立建屋总局,在各地方城市设立建屋分局,根据规划,合理地确定每年修建组屋的数量,上报规划得到国家批准后,开始执行计划。央行设立“建屋基金”,专门为此配套增发货币,无息贷款给建屋局。”
“建屋局建设使用的材料,包括水泥、钢材、木材、砂石,玻璃、其它建材等,全部纳入国家特别计划,保障供给。原则上是以成本价加上不超过5%的利润,供给建屋局。相应的供应商在这种生意中,不是没有收益,虽然利润微薄,但这是最稳定的生意,帮助他们养活了员工,消化了大量经营成本,而且扩大产能的话,因为规模效应,他们的平均成本还会下降,而他们其它的生意,就可以获得更高利润。”
“而建屋局使用的建设用地,地方政府划拨,基本上是零成本。”
“人工上,鼓励城市和乡寨,发展各种建筑公司,建筑公司的主要形态,应该是混合制企业,这不是战略行业,无需国家完全控股,但为了预防私人建筑公司,偷工减料,所以需要一定的国有股成分,进行监督。凡属组屋的建筑工程,对于利润也是卡得很紧的,例如只有10%。但同样,这样的生意对建筑公司还是很有意义的,无论是养活队伍、积累经验还是稳定经营。”
“这样,通过土地、建材、人工等环节全面的最低成本化,就可以让组屋的建造,降低到最低成本,以前世的房地产成本结构来观察,大约70%是土地成本,30%是其它成本,于是,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土地成本几乎是0,而30%的其它成本可能下降到了15%~20%,所以,按照这种模式建筑同等质量的组屋,成本可以控制在市场化情况下的20%,这就让地方政府有了巨大的余地。”
“成本是20%,我们假设,允许地方政府以50%的价格出售,这是2。5倍的价格,利润高达30%,这就满足了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中获得城建资金的需求。”
“对于购房者来说,原来市场化的价格,如果是房地产成本的120%,而现在则是50%,他们购买所花的价格,就只有市场化水平下的40%出头,房地产这座大山的压力,就大大地降低了。”
“另一方面,大部分的购房者仍然需要房贷,对于房贷,必须严格限制银行贷款的利息率,各银行要设立“组屋专项贷款基金”,可以向央行争取增发货币,经过央行审核而定。我前世房贷的利息,名义上是8%左右,实际上那是银行玩弄的数字游戏,实质利率高达百分之十几,是非常高的利息水平。正常情况下,我们必须将人民承担的利息控制在6%以下,以进一步压低房地产对于城市居民的负担。”
“每家购买组屋,只能是单独的一套,是完全的房住不炒,而且如果搬迁卖出,只能是卖回给建屋局。那些小富人如果不满意,可以放弃组屋,去购买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对于商品房,国家将课以重税,务必将其单位成本拉高到组屋成本的5倍以上,售价拉高到组屋的3倍以上,恢复到市场化和商业化环境下的高价房产,让普通的人民,根本不会去考虑购买这类房屋,且银行的贷款条件需要非常严苛,不能让这部分商品房,有金融杠杆炒作的可能性。”
“从这部分商品房,政府就可以按照香港模式,获得地价收入和房产销售税收。”
“需要设立独立的建屋监督局,监督方向是两个,第一个是保障建屋的各环节质量,哪个环节拉胯,就严厉追究那个环节的法律责任;第二个是对各城市建屋的数量,进行严密调查,数量必须满足需求,数量也不能过多而浪费。组屋建筑的数量,本质上是由建屋监督局控制的,而非地方政府。”
“主席,从金融的角度看,这种货币的增发就是一种“精准定向增发”,对于其它经济面的影响,就会最小化,也不易引起通货膨胀。”
主席点点头,感慨地说:“建设社会主义,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目标。经济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你这个房子的方案,我觉得尝试一下是完全可行的。”
李思华认为医疗问题,解决的难度比起房地产更大。她接着说:
“主席,为什么我觉得医疗的问题更大呢?因为现代医疗,主要是依靠西医和西药的手段。”
李思华前期确定了“中医为养、西医为治”的总原则,本身也是不得已,想依靠中医来完全解决医药的问题,不现实。西医师经过大学教育之后,至少能根据严格的数据标准开药,或者开刀治疗。西药这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基本上能够标准化。但中医就不行了,高度依赖中医师的个人水平,难以量化,所以会有很多“庸医”出来,从现代化国家的角度看,只能是辅助,不能作为主体。
“西医为主,就会有很多深层次的的问题产生。”
“首先是西药,大量的西药是有“专利”成本的,除非未来我们完全不承认国际的专利,自己仿制,但这样将严重影响国际贸易,专利体系是欧美进行贸易的根本基础,他们就靠这个体系获得高额收益,这是“合法剥削”的一种。所以不承认专利,只是一种备手,是在我们与西方彻底交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的极端措施。但这样也得不到生产新药的配方和技术。所以正常情况下,西药的成本就比较贵。”
“其次是西医,西医采用大量的先进设备,这些设备同样包括专利成本,卖得非常贵,我们目前的现状还必须大量进口,虽然前期工业基础搭建的时候,也包括了一些医疗设备的生产,但那都是最基础的部分,而最近几十年,会有大量的新设备被发明出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发能力,肯定是需要大几十年去追赶的。”
“医生当然更是问题,培养的速度快不起来,这不仅是教育,还需要大量的医疗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