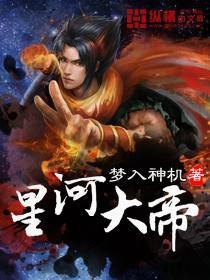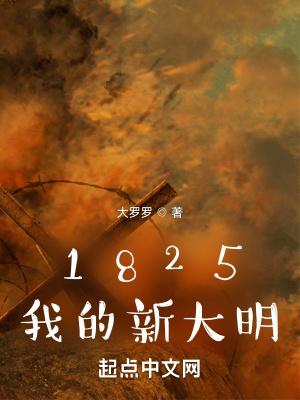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赴青山什么意思 > 雨夜(第1页)
雨夜(第1页)
深夜时分,初春的第一场细雨,便这么毫无征兆的落了下来。雨声淅淅沥沥,泠泠作响,陆晚在半梦半醒之间,睁开了双目。重生回来的这些天里,许是因为前世的心结,她一直睡得不太安稳。怔愣片刻后,她自榻上起身,随手披了件外衣,缓步行至窗前。
她推开窗户,恰好与料峭的春风撞了个满怀。寒意漫进周身,陆晚不由得拢紧了些身上的外衣。她垂眸,目光触及窗外的蒙蒙细雨,忽然忆起了前世里的一个雨夜。
那是建宁十二年的三月廿五,惊蛰日,正是雨水多发的时令。
彼时的江淮安已经顺利通过了殿试,成为新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负责修史、起草召令等工作。陆晚的父亲,陆正,非常欣赏这位朝廷新贵,时常邀请他入府共同商议与赋税变革有关的要事。
那天,江淮安与陆正在书房里商讨了许久,不知不觉已至酉时。天色昏黑,万里无云,慢慢地便有豆大般的雨点从天而降。
陆正见雨势渐大,又加之其有意撮合自己的女儿与江淮安,便让陆晚撑伞送江淮安归家。
春雨如帘,霏霏而下。纵使撑伞而行,仍避不了雨水沾衣。方跨出庭院不远,陆晚的身上绿罗裙便湿了一半。
一场春雨一场寒。寒凉的雨水垂打在身上,陆晚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打了个寒颤。
“陆姑娘,稍停片刻。”
温润清明的声音在这静谧的雨夜里显得格外入耳。陆晚脚步一顿,不由侧目去看身旁的年轻男子,却忽觉肩头传来一阵轻而稳的暖意。她下意识垂下目光,却见肩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件月白色外袍。
她愕然抬眸,见眼前人冲她弯了弯唇:“雨夜湿气重,姑娘切莫着凉了。”
“伞交由我撑着吧。”
一种不知名的情绪在陆晚心底滋生开来,她递过手中的雨伞,抿唇道:“多谢江公子。”
“无妨。”
江淮安原先在燕京的西胡同里租了一间房子。后来,他进士及第,便住进了高坡巷里的官舍。高坡巷离陆府不远,大约一刻钟便可抵达。
一路上,因着梅园初见的机缘,两人也并不生分,偶尔会闲谈片刻,聊的内容大多都与诗词歌赋有关。
陆晚有幸从陆正那里读过江淮安的诗文,深爱其平淡深静的诗风。如今又与他共伞对谈,便更对他多了几分钦佩与仰慕之情。
谈至尽兴之时,那人蓦然没了声音。陆晚微微诧异,却见男子将伞还递于她:“姑娘不必再送了,江某已经快到家了。”
“可是——”陆晚不解,这里明明离他的官舍还有几步之遥,正欲开口询问,却见他疾步奔向不远处的街角。
雨落不止,斜织成线。隔着雨幕,陆晚的视线有些迷糊。她微微往前凑近了些许,便瞧见了这样一副场景——街道的角落里,单衣湿透的年轻男子自袖中掏出了一袋碎银递给了一位衣衫褴褛的乞儿。
陆晚知道江淮安是寒门出身,自幼由嫂嫂抚养长大。他刚刚任职,俸禄也只够糊口。
陆晚终于明白父亲为何会如此欣赏这位年轻的书生了。很多时候,善意只是一种选择。有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却不肯施半分怜悯给旁人;亦有人半生孤苦,却甘愿冒着风雨对一位素不相识的乞儿施以援手。江淮安就是后一种人。
亲眼目睹此情此景,陆晚忽然有种冲动。这种冲动出自于她的本能,她甚至都没有思虑一番,便径直向街角走去。
街角并不宽敞,江淮安的半只身子都淋在了雨里。他此时正在轻声安抚眼前的乞儿,并没有意识到陆晚已经立在了他的身后。
“江公子。”
闻言,江淮安眸子里闪过几丝惊讶,他侧过身子,与陆晚相视:“陆姑娘,你还没有归府?”
陆晚笑笑,尚没有回应,只是缓缓解下江淮安方才披在她身上的月白色外袍,而后朝着蜷缩在角落里的乞儿走近,将外袍轻轻裹在了他的身上。
“江公子,我再送你一程。”
江淮安微愣,垂下眼看面前的姑娘。寒雨淋漓的夜里,她周身的衣裙早已半湿,执伞的手却未动分毫,面色平和安然,没有半分不耐。
江淮安自幼习儒,生性安静内敛,是以相比于旁人,他在男女之情上实在是钝感了许多。譬若此时,面对着眼前的姑娘,他心底滑过一丝奇异的情愫,却不知这丝情愫究竟为何。
他半晌才收回了目光,答谢道:“有劳姑娘了。”
陆晚将江淮安送至官舍时,两人都是湿衣蔽体。江淮安怕她着凉,便将自己的一件玄色披风递给她,暂时遮身,而后又亲自煮了一碗姜茶给她祛寒。
陆晚离开之际,天色较之前又暗了几分。江淮安顾念她的安危,便又亲自将她送了回去。
二人于陆府门口离别之际,陆晚忽而叫住了正欲背身离去的男子,她平素镇定,此刻的声音却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希冀与慌乱:“今夜多亏了江公子。”
奈何夜色深沉,不然此刻江淮安转身之时必定可以瞥见眼前女子的耳根已经泛起了几分薄红。
可惜他并未瞧见这些,因而只是含笑道:“是我该谢过姑娘。姑娘执伞相送,陆某不胜感激。”
陆晚的回忆停留在了江淮安最后的那个温朗和煦的笑容上。此时,雨已经停了,或许是因为这份不可多得的美好回忆,陆晚竟难能地多了几分睡意。
一场春雨过后,天色愈加明朗澄澈。断虹霁雨,青山如黛,甚是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