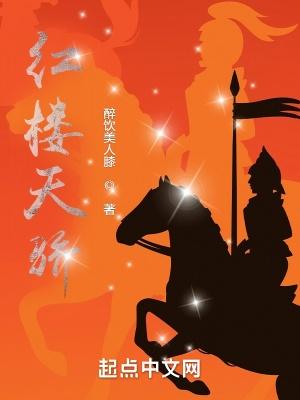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宫斗经历 > 第44章(第1页)
第44章(第1页)
那些人心黑着呢,肯定恨她入骨,毕竟她的存在,损失了他们的利益,整她很正常。
……
太后在御书房铩羽而归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了前朝后宫。皇帝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不仅震慑了六宫,更让前朝的某些人感到了深切的不安。
文渊阁内,烛火通明。
几位内阁大臣并未散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凝重。首辅杨廷和面容沉静,指尖缓缓捋着胡须,听着阁臣语气激动地陈述。
“……陛下此举,实乃骇人听闻!纵容后宫妇人滞留御书房,已是破例,如今竟为了那李氏,公然顶撞太后,还杖责宫人,下达那般严旨!长此以往,祖宗家法何在?朝纲体统何存?”
这阁臣是太后一脉,更是传统礼法的坚决维护者,今日之事让他倍感羞辱与危机。
谢迁听着叹了口气,想到这几天的槽心事眉头紧锁:“陛下年轻气盛,一时被美色所惑,也是有的。只是这李氏,确非寻常女子。她所为‘摘要条陈’之法,看似便利圣阅,实则已触及奏章批答之权柄核心。潜移默化,其害甚巨啊。”
他们都不是蠢人,皇帝那句“节省数个时辰,更清晰地洞察国事”像一根刺,扎进了他们心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以往那些经过斟酌、修饰甚至模糊处理的票拟,在皇帝面前可能变得漏洞百出!意味着贵妃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影响皇帝决策的通道。
这简直动摇了文官集团经营多年的权力根基。
一直沉默的杨廷和终于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陛下之心已决。直言强谏,恐适得其反,更伤及君臣之情。”
他目光扫过同僚:“然,纲纪不可废,礼法不可堕。陛下可护她于御书房一时,却护不住这宫闱朝堂的每一处。”
谢迁向他看去,“首辅的意思是?”
杨廷和端起茶盏,杯盖拨弄着浮沫,语气淡然:“贵妃之能,在于近。然宫中事务,绝非只有御书房一处。六局二十四司,偌大宫廷,千头万绪,总有其力所不及之处,亦有其不得不遵循的规矩。”
他放下茶盏,声音微沉:“听闻承乾宫用度奢靡,远超妃位份例?且宫中饲养猛兽为宠,虽陛下特许,然终究于礼不合,更有安全隐患。这些,皆乃后宫之分内事,太后娘娘凤体欠安,无暇顾及,我辈臣子,为陛下声望着想,提请皇后娘娘过问一二,亦是本分。”
谢迁立刻领会:“首辅高见。此外,闻听那东厂新提督闻溪,原是承乾宫首领太监?如此骤登高位,难免引人疑虑。东厂乃国之利器,岂可沦为私宠爪牙?厂卫之中,亦多有忠正之士,岂会甘受阉竖驱使?若有些许不平之鸣上达天听,亦是常理。”
这几天东厂的不平之鸣可太多了。
李东阳补充道:“闻溪新官上任,便在厂内大肆清洗,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弄得怨声载道。此乃现成的把柄。”
谢迁点点头:“其次,陛下近日因贵妃之故,对政务似乎过于勤勉了?”
他这话说得含蓄,但在场所有人都明白其意,皇帝以前贪玩,现在勤勉的方向却是因为一个妃嫔,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信号。
“陛下年少,精力过人本是好事,但若方向有偏,则易被小人利用。”杨廷和沉吟道,“或可寻一二无关痛痒却又繁琐耗时的政务,呈报陛下,一来试探,二来亦可令其知难而退,或至少无暇他顾。”
“其三,”谢迁再次说道,“祖宗家法,后宫不得干政。太后出面虽未成功,但此言大义仍在。我等可联名上奏,不必直指贵妃,只泛言规劝陛下恪守祖制,远离女色,勤修圣德,言辞恳切,以情动之,以理喻之。天下士林清议,亦当为此发声。”
天下读书人,哪一个不向着内阁,哪一个不是男人呢?
他们可看不得女人当政,那群情激奋的辱骂不需要上面推波助澜,下
面的酸儒根本收敛不了一点。
杨廷和微微颔首,不再多言。
策略已定,避其锋芒,迂回侧击。一是从后宫规矩入手,对李凤遥的日常用度、行为规范进行挑剔和约束,让她在承乾宫之外处处感到掣肘,疲于应付。
动摇其羽翼,将矛头指向闻溪,斩断李凤遥伸向前朝最有力的一只手臂。
制造舆论,士林清议贵妃干政,佞幸当道,逐步败坏她的名声,从道义上施加压力。
这并非疾风暴雨般的弹劾,而是如同春雨般无声无息的渗透和包围。每一件都是小事,都打着“维护宫规”、“体恤圣誉”、“澄清吏治”的旗号,让皇帝即便想维护,也难以次次都大发雷霆。
一次两次还有耐心,这些多了,皇帝就倦了累了,自然就会将她赶回后宫,根本不需要内阁与皇帝撕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