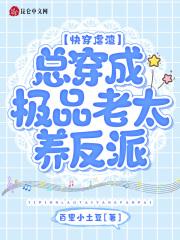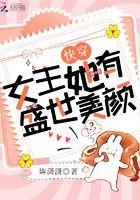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被疯批太子强夺后小娇娇 > 4第 4 章(第1页)
4第 4 章(第1页)
殿内,灯架散出的光亮映衬出一室明黄。
张太医刚为皇上把完脉,垂眸沉思了会儿后,缓缓开口道:“具臣细察,皇上脉象已经平稳,只是血行不畅,仍需注意调理。”
“但相比于前些日子,情况已经转好,待臣先对照古籍搜寻一番,好寻出个调理的法子来。”
景渊帝听完面露喜色。昨日昏睡了一夜,谁料今早醒来,却觉浑身通畅,他挥手送别张太医,重重道了声赏。
这时太监推开菱花隔扇门,两道身影一前一后入了殿。
谢斐走在前,白衣温润,轻轻笑着:“何事让父皇这般高兴?”
张太医正收拾药箱,闻太子疑惑,便将古籍的事情解释了一番。
未料谢斐听完,很是认真道:“这些日子,孤也很是担心父皇的病症,终于托人寻到了几册郑先生的孤本,不知张太医可用得上?”
郑先生乃前朝神医,临死前,将自己一生所遇的疑难杂症都抄录成册。只是自他隐世后,世人便再未寻到过他的踪迹,连带着那些书一同没了音信。
习医之人终其一生,不过都在寻觅他所留下的药方。
张太医激动地双手颤抖:“劳太子殿下费心,假以时日,微臣定能调理好皇上的身子……”
“张太医严重了,”谢斐忽然打断道:“并不是什么费心的事,父皇久病不见好,孤也很担心,能为父皇分忧,本就是孤应该做得。”
说着话时,谢斐眸色变得很淡,语气也染上一丝愁意。他静静站在殿中,看向景渊帝的目光温和真切。
景渊帝不禁有些感动,提起:“清辞,朕今日处理政务,沈于仲难得夸人,却对你回洛阳后的行事作风夸赞有加,朕当时就想传言所虚,朕看着你长大,你是什么性子,朕再清楚不过。”
谢斐幼时丧母,景渊帝本就更为偏爱他,曾亲自辅导过他的功课。多年过去,父子之间的情义或许因为时间淡了些,但也绝非一些没有证据的流言能阻。
像此刻,谢斐也只是谦卑地笑着,担忧上前:“父皇病中还不忘处理政务,儿臣自愧不如,只是身子重要,还望父皇勿要劳累过度。”
“殿下说得对,”正欲离开张太医听见此话,也语重心长地叮嘱道:“皇上如今血行不畅,当忌劳废心神之事,万事还要以龙体为重呐。”
要说这两番话可谓是说到景渊帝心坎上了。自病后,本就该事事以养病为先,可中书省那些个人,非但不体谅他,更是大清早就派人过来叨扰。
临窗的书案此刻还铺满了奏折,厚厚几摞堆起来,景渊帝越看越觉心烦,只是他一时忘了来送奏折的那位通事郎唤何名姓。
内侍很有眼色地上前提醒:“皇上,那位是年初才进中书省的郑通事郎,正在偏殿候着,可要奴才将人唤来?”
景渊帝点点头,很快内侍带着一道人影进殿,景渊帝拖长语调:“郑卿啊——”
被念到名姓的郑通事郎面色一白,他还在想那奏折是何时被替换的,忽感受到一股不好的预感。
景渊帝悠悠道:“朕想,这些日子堆积的政务,便送去东宫,暂由太子代政。”
暂由太子代政。这几字落下的瞬间,心中惶恐落实,那位郑通事郎双腿一颤,还没来得及说话,又被方才那内侍往外引。
几乎是被拖出殿外,他颤颤巍巍回过头,见日光透过窗棂,年轻男人的身影此刻沐在光下,而后从容不迫地拱起双手,不疾不徐道:“儿臣愿为父皇分忧,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期。”
隔扇门很快被合上。又走来一位内侍领人撤下奏折,临窗的书案重回空荡,桌面干净不染一丝尘灰。
*
后宫不可涉政,自进殿后,江听晚便一直规矩地候在角落。
直到宫女送来熬好的药,她才敢抬起眸,端着药碗小心翼翼朝里走去。
内室里明黄色帘帐半掩,景渊帝情况好转,当下半靠在榻边,身前是一身白衣的谢斐。
男声温和,不疾不徐:“禁足的这些天,枯坐于桌前,总想起幼时,父皇忙里抽闲教我念琴,那时还不懂父皇用心栽培,现下想来,儿臣总有些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