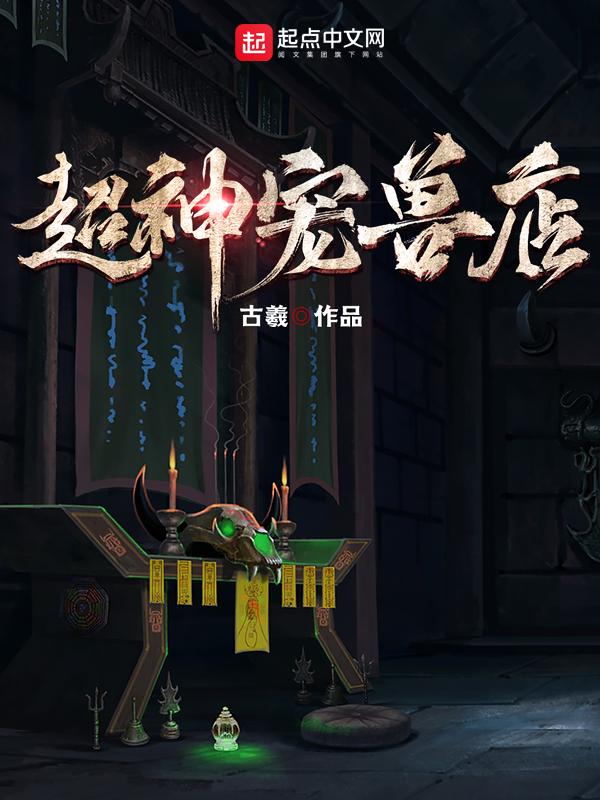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州郡失据的意思 > 第6章 女捕快的屈辱(第6页)
第6章 女捕快的屈辱(第6页)
母亲听到后咬着嘴唇,眼神低垂,对我低声道:“明石,去街口买些墨。”
听到后我迅速起身,低头假装离开,绕到柴墙的小洞,果然看到陈安将她压在床榻上,提起母亲那双修长的美腿在腰际,掏出肉棒在那里抽插,从房间中不断传出母亲低绵的呻吟声。
甚至某日傍晚,屋内烛光未点之时,我正在抄写卷宗,母亲刚从衙门归来,官服沾满尘土,疲惫不堪。
陈安就在后面推门而入,这次还没有等他说话,母亲就声音颤抖地对着我道:“明石,去后院劈柴。”
我立刻点头出门,心跳如雷,绕到小洞旁,看着陈安撕开她的官服,迫使她跪在床榻上,从后面侵犯,房间中那朦胧的靓丽身影已经成为了我下体躁动的源泉,我发现我其实更想看到母亲被人玩弄,每次看到母亲被人征服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下面兴奋起来。
就这样日子过去了一天又一天,某日清晨,阳光透过窗纸洒进屋内,我正在整理卷宗,母亲在灶台旁煮粥,突然看到有人进来,我立刻心跳加速,正准备照例离开。
这时候母亲也一如往常般无奈地低声道:“明石,去库房取些纸张。”
我点头正要出门,却见陈安推门而入,这次他目光冷淡,扫了母亲一眼,语气平平:“向捕快,今日无事,忙你的。”说完他转身离开,锦袍衣摆在晨光中一闪而过,留下屋内一片死寂。
母亲愣在原地,手中的铜勺微微颤抖,眼神复杂,似松了一口气,嘴角甚至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解脱。
她缓缓放下铜勺,整理官服,低头继续煮粥。
我站在门槛旁,胸口却燃起一股欲望难填的躁动感。
从那日起,陈安对母亲的来访骤减,隔三差五的推门变为偶尔一次,甚至后堂的招待也不再召她。
母亲也慢慢恢复了过来,重新将精心放在办案上,她眼底的疲惫少了分屈辱,多了分冷峻的平静。
我却无法平静,每晚抄写卷宗,看着身边母亲安静的样子,我的脑海却总会浮现她被陈安压在床榻上的画面挨肏的样子,以及母亲赤裸的肌肤泛着汗光,在床上呻吟的淫荡样子,母亲曾经的样子已经让我难以忘怀,我想要更多。
此后我继续在县衙抄写卷宗,同时也会关注官府书房,某日深夜,我在书房角落发现一叠古旧文书,隐约提及“血莲刹”与“迦罗”。
我屏住呼吸,小心翻阅,得知血莲刹这一织织早就存在于东州,他们来自东州以东的迦罗之地,属于性力派一支,崇尚肉欲与神秘仪式,早已在东州扎根百年。
文书还提到同期进入东州的“业魔杵”,来自高原属金刚宗的一支,与血莲刹似有关联。
血莲刹本并不是非法组织,但他们在南临的一些案件中有所涉及,母亲曾查到线索,却被陈安强压了下去。
此时我正抄录关键段落,忽闻脚步声逼近,心跳如雷,匆忙将文书塞回原处。
突然陈安推门而入,看到我却奇怪地笑了笑,他未将我捉拿,而是走近,然后低声在我耳边道:“向明石,你这小子机灵,查血莲刹的底细?哼,本官早知道你偷看的心思。”他的声音低沉,带着戏谑,“每次本官肏你母亲,你都趴在小洞旁,手在裤裆里忙活,兴奋得跟条狗似的,对吧?”
我脸色霎时苍白,却又无法反驳。
这时他冷笑继续:“你那点禁忌心思,藏不住的。想不想再多看看?她那腰肢、那屁股,那叫床的声音,够骚是吧!”他拍了拍我的肩,语气充满着循循善诱,“放心,已经有其它人看上了她,他们过几天就来。你继续当你的瞎子,躲在门外看戏,保管更刺激!你若听话,好好学他们的语言,本官保你前程无忧。”
他的话如毒蛇一般钻进耳膜,羞耻感烧得我脸颊发烫,可心底那股禁忌火焰却被他点得更旺。
母亲的胴体、她的呻吟、被玩弄的模样,在我脑海中不断炸开,我无法否认,他的诱惑让我心动了。
从那日起,我与陈安的关系变得微妙,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
他时常召我到书房,表面讨论文案,实则低声调笑,循循诱导我承认对母亲的禁忌渴望,甚至暗示我主动上手,弄得让我心神摇曳,欲火与羞耻交织。
数日后,官舍木门外陈安再次出现,母亲立刻红着脸低声道:“明石,去县衙整理卷宗。”我低头应是,心跳如雷,假装出门然后绕到一直躲着的小洞中,目光死死锁住屋内的光影。
母亲的声音略带抗拒和羞辱,“陈大人,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只见陈安嘿嘿一笑,轻轻抬起母亲的脸颊:“怎么,想挨肏了?”
母亲红着脸将头扭过一旁:“请大人自重。”
说完,陈安一如既往地脱下母亲的衣服,将她推到床上,分开她的双腿开始享用,而母亲也在他的玩弄下达到了久违的高潮。
然后陈安完事之后站起来,正当母亲以为结束的时候,突然间一群肤色黝黑的外族人走了进来,他们三五成群,衣衫肮脏,散发着咖喱与汗臭的怪味。
他们不会中原语,操着生硬的迦罗腔调,眉间点着朱砂,腰间铜铃叮当作响。
“今天开始,伺候他们,记得要好心伺候,这些可是我的‘贵客’。”
陈安正打算转身离去,母亲却不知所措,只见她光着身子将手伸向知府:“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伺候这些外人,这不行,不要啊。”
说完母亲转身正打算去拿刀,却被陈安一眼瞪住:“都说了,这是我陈府的客人,不得怠慢。”
“陈,陈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