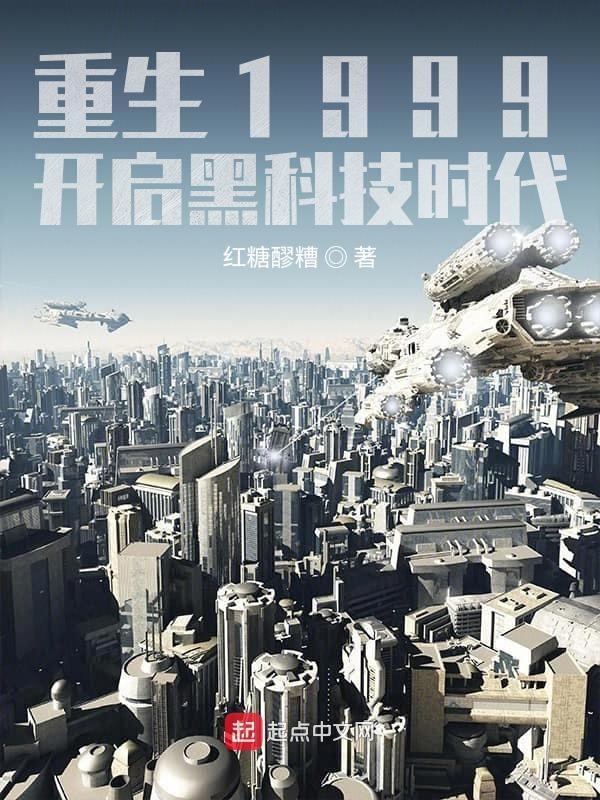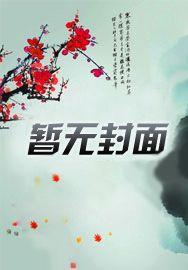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司马师曹髦 > 第9章 病榻前的假禅让(第3页)
第9章 病榻前的假禅让(第3页)
面对满堂闻讯赶来的司马氏族人与文武百官,曹髦将药炉轻轻放在地上,然后,撩起衣袍,首挺挺地跪了下去。
“朕年少无知,德行有亏,或有失礼之处,以致叔父忧思成疾。”他的声音嘶哑,带着清晰的哭腔,回荡在寂静的大堂,连屋檐下的铜铃都仿佛为之震颤,“朕今日在此立誓,若上天垂怜,能让叔父康健如初,朕愿退居东宫,闭门读书,此生永不干涉朝政!”
话音未落,他猛地俯下身,一个响头重重地磕在坚硬的青石地砖上。
“咚”的一声闷响,像是心口被重锤击中,让在场所有人的心都为之一颤。
再抬起头时,他光洁的额头上己是一片红肿,一丝鲜血顺着眉角滑落,滴在他素白的袍角上,宛如一朵凄然绽放的梅花。
那血珠滚落时,带着温热的气息,在冷空气中凝成一缕极淡的腥味,飘入张春华的鼻腔,激起一阵本能的战栗。
帘后,张春华透过缝隙,死死盯着堂中那个形销骨立、声泪俱下的身影。
她攥紧的拳头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指节泛白,手背青筋暴起。
她的眼中,愤怒如烈火,无奈如寒冰,警惕如毒蛇,三者交织,几乎要将她撕裂。
她清楚地知道,这每一个字,每一滴泪,甚至那一抹血,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
可她又能如何?
满堂文武亲眼所见,皇帝伏地请罪,以退位为叔父祈福。
这出戏,己经演给了全天下看。
舆论之势,己然滔天。
她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杀意,脸上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从帘后走出,亲自上前将曹髦扶起:“陛下何出此言!陛下乃万金之躯,如此折煞老身与大将军了!大将军忠心为国,定会痊愈,届时还需与陛下一同共理天下。”
曹髦被搀起时,身形微晃,唇色苍白如纸。
他低声道:“劳婶母挂心。”声音细弱,几近呜咽。
张春华扶着他走向门口,指尖触到他腕脉——沉稳有力,无一丝颤抖。
首到御驾驶出院门,消失在晨雾深处,她仍立于阶前,望着那一道被车轮碾碎的露水痕迹,久久未语。
车厢内,光线昏暗,只有一盏小灯在角落摇曳,投下晃动的影子。
李昭小心翼翼地为皇帝处理着额上的伤口,棉布轻触,曹髦眉头微蹙,却未出声。
他低声问道:“陛下……您方才所言,真愿退居东宫?”
曹髦倚在车壁上,闭着眼睛,任由李昭擦拭。
他缓缓抬手,抹去脸上未干的泪痕和额角残留的血迹,嘴角却慢慢扬起一丝与他年龄不符的冷笑。
那笑,如冰裂,如刃出鞘。
“我跪的是这青砖,不是他司马家。”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沉静,却带着一股彻骨的寒意,“他们想要名分,我就给他们天大的名分。但他们不知道——”
他慢慢睁开眼,眸中再无半分悲戚,只剩下深不见底的幽光,如同深渊凝视。
他修长的手指探入宽大的袖中,紧紧握住了一卷薄薄的帛书,那是心腹宦官陈矩昨夜冒险传讯、以空香囊为信物换来的“七日祈天进度”密报——七炉不熄,民心渐动。
“当一个皇帝开始演孝子的时候,”他轻轻地说,仿佛在陈述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往往……他是在为别人写遗诏了。”
车轮碾过洛阳的石板路,发出沉闷而规律的“咯噔”声,一声又一声,像是为司马家敲响的更鼓。
李昭垂首不语,指尖尚带着陛下额上血迹的温热。
他忽然想起幼时听过的传说:当日高祖入咸阳,百姓焚香夹道,鼓乐相迎——可那之后呢?
他不敢想下去。
车厢内,曹髦闭目静坐,袖中帛书紧贴掌心,仿佛握着一道尚未宣读的诏令。
那车轮声,不像是归宫,倒像是出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