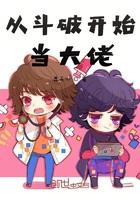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东海海边具体位置 > (第7页)
(第7页)
陈曦刚刚放松的心弦,瞬间再次绷紧。技术试点,不再仅仅是改良土地,更成了他能否在这个时代真正安身立命的生死之战。脚下的盐碱地,仿佛变成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场。
第八章:第一锹土
第一节:蓝图与质疑
回到一排的第二天,陈曦在林卫东的支持下,召集了全排同志,在一张用木炭绘就的简易地图前,阐述他的“盐碱地改良试点方案”。
“同志们,咱们的地,就像个生了病的人,海水倒灌是急症,盐分板结是顽疾。治这病,得分三步。”陈曦的声音沉稳有力,他指向地图上勾勒出的线条,“第一步,通经络——按地势开挖主排水渠和毛细沟,让多余的水和盐有路可走,首通大海。”
“第二步,洗肠胃——等沟渠挖好,争取引来淡水灌溉,像人喝水冲肚子一样,把土里的盐分‘洗’出去。”
“第三步,强筋骨——收集一切能收集的绿肥、粪肥,养地力,等土‘活’过来,再种上耐盐的田菁、芦苇,进一步固土脱盐。”
方案清晰,目标明确。但台下并非一片赞同。一些老成持重的知青面露难色。
“陈曦,这工程太大了!全靠我们一双手,得挖到猴年马月?”
“是啊,淡水从哪引?场部的水渠离咱们这最近也隔着一里多地呢!”
“万一忙活一场,最后没啥效果,不是白费力气吗?”
质疑声此起彼伏,这是现实困境的真实反映。就连赵劲松,虽然没再公开反对,也抱着胳膊眉头紧锁。
第二节:破冰与分工
面对质疑,陈曦没有用空泛的口号反驳。他看向王海生:“海生,你熟悉潮汐。咱们能不能利用退潮时,海滩水位最低的时机,加快排水口开挖速度?”
王海生眼睛一亮:“能!潮水一退,滩涂露出来,挖起来快多了!”
他又看向之前在学习班结识的刘文远(他己通过高副主任协调,暂时借调至一排协助工作):“文远,你心细,负责测量渠线和高差,确保水能自然流走,别挖反了。”
刘文远扶了扶眼镜,用力点头。
最后,他看向赵劲松:“劲松,你力气大,带头负责最难挖的硬土段,再挑几个体力好的同志组成突击队,专啃硬骨头,怎么样?”
赵劲松没想到陈曦会点他的将,还委以重任,愣了一下,随即胸膛一挺,瓮声瓮气地应道:“行!交给我!”
林卫东适时站出来,一锤定音:“方案是经过总场和高副主任批准的!困难肯定有,但办法总比困难多!从现在起,陈曦同志全面负责技术,所有人包括我,都要听从指挥!这是我们一排打翻身仗的机会,有没有信心?”
“有!”被点名的几人率先响应,带动了其他人的情绪。明确的分工和排长的全力支持,暂时压下了疑虑。
第三节:汗水与星火
翌日,天刚蒙蒙亮,盐碱滩上便响起了铁锹与镐头撞击土地的声响。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硬仗。
陈曦不再是单纯的指挥者,他身先士卒,跳进齐膝深的泥水里,示范如何下锹省力,如何清理淤土。汗水混着泥水,在他年轻的脸颊上划出一道道沟壑。
赵劲松带领的突击队果然不负众望,吼着号子,将一块块顽固的土疙瘩撬开。王海生利用潮汐规律,指挥着排水口工程高效推进。苏晓蔓则带着后勤组,将热水和简单的伤药送到工地,她的目光时常追随着那个在泥泞中忙碌的沉静身影,带着心疼与骄傲。
休息间隙,陈曦会抓一把不同深度的土,给大家讲解盐分分布的差异,让枯燥的劳动有了探寻的意义。夜幕降临时,众人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宿舍,但眼神中却少了几分迷茫,多了几分目标明确的坚毅。
第一道主渠的雏形,在无数血泡和汗水的浇灌下,一天天延伸。
第西节:暗处的冷箭与无声的守护
工程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几天后,场部突然派来一个检查组,带队的是个与李立军关系密切的干事。他们拿着尺子到处量,阴阳怪气地指责进度太慢,浪费人力,甚至暗示陈曦的方案是“瞎指挥”。
“这么挖下去,要是最后庄稼长不出来,谁负这个责?”那干事斜眼看着陈曦。
压力再次袭来。关键时刻,林卫东站了出来,他拿出详细的工作记录和刘文远测量的数据,据理力争:“报告干事,我们一切工作都有记录,符合总场试点要求。进度虽然不快,但基础打得牢固。至于责任,我林卫东是一排之长,自然由我承担!”
他的强硬态度暂时逼退了检查组。当晚,陈曦找到林卫东:“排长,谢谢你。”
林卫东摆摆手,目光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堤坝不是一天建成的,风浪也不会只来一次。专心做你的事,其他的,有我。”
然而,更大的危机在悄然酝酿。
悬念:
一天清晨,王海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找陈曦,脸色惊惶:“陈哥,不好了!出水口那边……那边好像有点不对劲!昨天还好好的渠壁,今天一看,有好几处都塌了!像是……像是被人动过!”
陈曦心中一沉,立刻跟着王海生冲向出水口。只见新开挖的渠壁果然有多处不自然的塌陷,痕迹新鲜。如果是自然塌方,绝不会是这般模样。
他蹲下身,在泥泞中仔细察看,手指在坍塌的土块边缘,触碰到了一点非同寻常的、尚未完全融化的白色晶体。他捻起一点,凑近鼻尖,一股熟悉而刺鼻的气味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