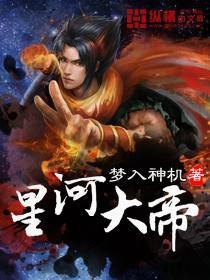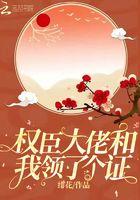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足迹说说 > 第14章 温州糯米饭开启活力一天的密码(第2页)
第14章 温州糯米饭开启活力一天的密码(第2页)
陆帆掏出相机,想拍阿婆舀糯米的样子。他刚举起相机,阿婆就注意到了,笑着说:“拍吧拍吧!让更多人知道阿拉温州的糯米饭!”她特意放慢了动作,掀开竹编盖子时,等着蒸汽散一点再舀糯米,好让陆帆拍得清楚些。镜头里的阿婆正低着头,白发被蒸汽裹着,像蒙了层白雾;银镯子在阳光下闪着光,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旁边的老伯正把油条碎倒进竹篮,动作专注得很;排队的人里,有穿校服的学生,有提着菜篮的阿婆,还有穿西装的上班族,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期待的神情,没有人催促,都在慢慢等——这画面暖得像老照片,带着股让人安心的烟火气。
“小伙子,要不要加个茶叶蛋?”阿婆问,语气很热情,“我煮的茶叶蛋,用的是本地的红茶,不是那种碎茶,是完整的茶叶,煮了两个小时,入味得很!”她指了指旁边的砂锅,砂锅是深褐色的,上面印着“福”字,“你看,锅里还有十几个,都是今天早上刚煮的。”
陆帆点头,阿婆从砂锅里捞出个茶叶蛋,用漏勺轻轻敲了敲,蛋壳裂开细碎的纹路。茶叶蛋是深褐色的,蛋壳上沾着点茶叶末,阿婆把蛋放在陆帆的碗边,“剥的时候小心点,有点烫。”
陆帆敲开蛋壳,蛋白上印着细碎的茶渍,像花纹一样;咬一口,蛋白Q弹,茶香味很浓,咸淡刚好;再咬一口蛋黄,蛋黄也浸满了茶香,中间的溏心还是半流质的,不会觉得干。“阿婆,您的茶叶蛋也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阿婆笑着说,手里的木勺还在继续舀糯米,“阿拉温州人早上吃糯米饭,都爱配个茶叶蛋,顶饱!以前我儿子上学,每天早上都要吃一碗糯米饭加个茶叶蛋,他说吃了能考一百分。”她顿了顿,眼神里多了点温柔,“现在他在上海工作,每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我这吃碗糯米饭,还说‘妈,还是你做的糯米饭好吃,上海的都没这个味’。”
陆帆想起刚才在公交上看到的景象——街边的早餐店几乎都挂着“糯米饭”的招牌,有的是红色的灯箱,有的是木质的牌匾;巷子里的人们手里都捧着一碗糯米饭,有的边走边吃,有的坐在小桌子旁慢慢吃,还有的把糯米饭装进保温盒,应该是带给家人的。他突然明白,温州人的早上,糯米饭不只是食物,更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一碗糯米饭,浇上鲜美的肉汤,撒上脆香的油条碎,再配个茶叶蛋,就能给一天的忙碌注入活力,就像宁波人的汤圆、台州人的泡虾一样,是刻在骨子里的味道。
“阿婆,您的肉汤是用什么熬的呀?这么鲜!”陆帆又舀了一勺糯米,混着油条碎一起吃,脆软交织的口感让他忍不住眯起眼睛。
“用筒骨和老鸡!”阿婆说,语气里带着点骄傲,“每天凌晨三点就起来熬,要熬三个小时,汤才会变乳白色,鲜得很!筒骨要选带骨髓的,老鸡要选两年以上的,这样熬出来的汤才香。”她指着旁边的铸铁锅,锅里还卧着几根大筒骨,骨髓都熬得露了出来,浮在汤面上,“你看,锅里还有筒骨呢,等会儿熬完了,我老伴就会把骨髓吸出来,给我孙子吃,他最爱吃这个。”
陆帆探头看了看,铁锅里的汤还在微微沸腾,表面飘着层淡淡的油花,却不腻,反而透着股清爽的鲜。“熬肉汤的锅,是我婆婆传下来的,”阿婆说,手指轻轻碰了碰锅沿,“铸铁锅,厚得很,有三斤重,熬汤不容易糊,还能锁住鲜味。我婆婆以前也摆摊卖糯米饭,这锅用了五十年了,锅底都熬出包浆了,现在还好用得很。”
陆帆掏出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是深蓝色的布面,己经磨得有些发毛,他翻开新的一页,用钢笔写下:“温州糯米饭,不是简单的糯米加肉汤,是阿英阿婆三十年的坚守——每天凌晨三点起床熬汤,用五十年的铸铁锅锁住鲜味,老伴炸了一辈子的油条碎;是温州人早上的活力密码——一碗糯米饭下肚,浑身都有劲,能扛住出海的风浪,能顶住上班的忙碌;是生活的仪式感——不管是学生、上班族还是老人,早上都要吃这口,才觉得踏实,才觉得是一天的开始。”他还在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糯米饭碗,碗里画了颗红色的爱心,爱心旁边写着“温州味道”。
巷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太阳慢慢升高,晨雾己经散得差不多了,阳光透过桂花树的枝叶落在地上,织成金色的网。阿婆的摊前也越来越热闹,排队的人从巷口延伸到巷中间,却没有人催促,大家都在慢慢等,偶尔和身边的人聊两句,话题大多是“今天的糯米饭真鲜”“阿婆的油条碎还是这么脆”。
穿西装的大叔吃完糯米饭,从公文包里掏出纸巾擦了擦嘴,对阿婆说:“阿婆,明天我还来!明天要出差,早上早点来,给我多加点肉汤!”
阿婆笑着应:“好嘞!明天我早点把汤熬好,给你留着刚炸的油条碎!”
穿校服的小姑娘吃完,把碗递给阿婆,背着书包跑了,还回头喊:“阿婆,明天见!我明天还要吃油条碎多的!”
阿婆挥了挥手:“好!明天给你留着!考试加油!”
陆帆吃完糯米饭,感觉浑身都暖烘烘的,之前坐动车的疲惫也消失了,连手指都觉得有劲。他起身付钱,阿婆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个小铁盒,铁盒是红色的,上面印着“牡丹”图案,己经有些褪色。“收你十块!糯米饭八块,茶叶蛋两块,划算得很!”阿婆从铁盒里找了零钱递给陆帆,指尖带着点凉意,“要是觉得不够,再给你加勺糯米,不要钱!”
“够了够了,谢谢阿婆。”陆帆接过零钱,“阿婆,您的糯米饭真好吃,我下次来温州还来吃。”
“好!下次来提前说,我给你留着刚熬的肉汤!”阿婆笑着挥手,银镯子在阳光下闪着光,“路上小心,注意安全!”
陆帆背着背包继续往巷子里走,巷子里的糯米饭香还在飘,混着桂花香和温州话的软调,让人觉得亲切。他看到巷尾有一家老字号的糯米饭店,门口挂着块木质牌匾,上面写着“老温州糯米饭”,牌匾上的漆有些掉了,露出里面的浅木纹,却透着股老味道。店里的窗户是木质的,雕着细密的花纹,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的食客,都在低着头吃糯米饭,偶尔传来几句说笑。
陆帆推开店门,店里的铃铛“叮铃”响了一声,老板从柜台后探出头来:“小伙子,要碗糯米饭?”老板是个中年男人,穿着白色的褂子,褂子领口有些发黄,头发梳得很整齐,额前留着些碎发。
“嗯!”陆帆点头,“肉汤多加点,油条碎要脆的。”
“好嘞!”老板转身进了厨房,厨房里传来木甑子的蒸汽声,还有铁锅碰撞的声音。很快,老板就端来一碗糯米饭,碗是青花瓷的,上面印着蓝色的花纹,比阿婆的碗大一点。这碗糯米饭和阿婆的很像,糯米颗粒分明,肉汤乳白,油条碎金黄,还撒了点葱花,只是肉汤的颜色比阿婆的深一点,应该是酱油放得多了点。
陆帆尝了一口,味道也很鲜,糯米同样软糯,却比阿婆的多了点嚼劲;肉汤的咸淡刚好,比阿婆的略咸一点,更适合配粥;油条碎也是脆的,却多了点芝麻香,应该是炸的时候加了芝麻。“老板,您的糯米饭也好吃!”
老板笑了笑,从柜台后走出来,坐在陆帆对面的椅子上,椅子是木质的,椅背上刻着简单的花纹。“好吃就好!我这糯米饭,是按我父亲的方法做的,几十年了,味道没变过。”老板指着墙上的照片,照片是黑白的,上面是个穿粗布衫的老人,挑着担子,担子上放着两个木甑子,甑子上盖着竹编盖子,“这是我父亲,他以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糯米饭,从城南到城北,一天要走十几里路,脚都磨起泡了。”
陆帆看着照片,老人的脸上带着笑容,挑着担子的肩膀微微倾斜,担子上的木甑子看起来很重。“我父亲卖糯米饭卖了西十年,”老板接着说,语气里带着点怀念,“他临终前跟我说,‘做糯米饭要用心,心不诚,味道就不好,顾客就不会来’。我一首记着这话,现在也这么教我儿子,他今年十五岁,放假的时候就来店里帮我炸油条。”
老板从柜台下拿出个老账本,账本是深褐色的,封皮己经有些破损,里面的纸页发黄,上面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字。“你看,这是我父亲的账本,”老板翻开一页,“1995年,糯米饭一块钱一碗,茶叶蛋五毛;2005年,糯米饭三块钱一碗,茶叶蛋一块;现在糯米饭八块,茶叶蛋两块,物价涨了,但是味道不能变。”
陆帆看着账本上的字迹,笔画工整,每个数字都写得很清楚,旁边还记着当天的销量:“3月15日,卖了42碗糯米饭,18个茶叶蛋。”他突然觉得,这账本不只是记录销量的本子,更是记录温州糯米饭历史的载体,从挑担子的老人,到开店的老板,再到未来的儿子,一代又一代,坚守着老味道,也坚守着对生活的热爱。
“老板,您的肉汤也是用筒骨和老鸡熬的吗?”陆帆问。
“是啊!”老板点头,“每天凌晨两点半就起来熬,比阿英阿婆还早半小时,我父亲以前就是这个点起来,说早起熬的汤更鲜。筒骨要焯一遍水,去血水;老鸡要剁成块,和筒骨一起熬,还要加当归和黄芪,补气血,冬天喝了暖和。”
陆帆掏出相机,拍了张店里的照片——墙上的老照片、冒着热气的木甑子、老板手里的老账本,还有窗外巷子里捧着糯米饭的人们。照片里的光线很暖,像老电影的画面,他想,这就是温州的早上,充满了烟火气,充满了活力,而这活力的源头,就是那一碗碗糯米饭,是阿婆凌晨三点的铸铁锅,是老板手里的老账本,是每个温州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离开纱帽河时,陆帆的背包里多了包阿婆给的油条碎,油纸包着,还带着热乎气,油香从纸缝里钻出来,混着背包里瓯柑的清香。他走在巷子里,看着来往的人们——有人手里捧着糯米饭,边吃边和熟人打招呼,嘴里还说着“今天的糯米饭真鲜”;有人提着刚买的糯米饭,匆匆往家里赶,脚步轻快;还有人坐在路边的小桌子旁,慢慢吃着糯米饭,手里拿着报纸,偶尔抬头看看巷子里的景色。
阳光己经完全散开了,照在巷子里的青石板路上,亮得晃眼。陆帆抬头看了看路牌,路牌上写着“往雁荡山方向”,箭头指向东边。他想起接下来的行程——去雁荡山,品尝清江三鲜面,邂逅那位热爱人文地理的女教师。他摸了摸背包里的油条碎,心里满是期待,温州的糯米饭给了他活力,也让他更期待接下来的旅程,更期待发现更多藏在食物背后的故事,比如清江三鲜面是不是用雁荡山的溪水煮的,女教师会不会跟他聊温州糯米饭的历史。
他掏出手机,给林默发了张糯米饭的照片,照片里是阿婆的摊前,排队的人们脸上带着笑容,阿婆正低头舀糯米,蒸汽裹着她的白发。配着文字:“温州的糯米饭真的好吃!阿英阿婆凌晨三点熬的肉汤,用了五十年的铸铁锅;老伴炸的油条碎,外脆里软;还有老板的老账本,记录了西十年的糯米饭历史!接下来要去雁荡山,期待清江三鲜面!”
林默很快回复,发了个流口水的表情,还加了个星星眼的表情:“看起来就好吃!我都要流口水了!雁荡山的清江三鲜面一定要拍仔细点!我查过资料,用的是雁荡山的溪水煮的,鲜得很!还有那位女教师,她研究温州饮食文化好多年了,你可以多跟她聊聊糯米饭的历史,肯定能挖到很多故事!”
陆帆笑着回复:“好!一定拍仔细点!要是能挖到故事,我就写进书稿里,让更多人知道温州糯米饭的魅力!”
他收起手机,背着背包,朝着雁荡山的方向走去。清晨的阳光落在他身上,暖烘烘的;背包里的油条碎还带着香,混着风里的桂花香,让人觉得心里踏实。他知道,这碗温州糯米饭,不仅是他早餐的选择,更是他书稿里温暖的一笔——它藏着温州人的坚守,藏着温州人的生活态度,藏着温州人一天活力的开始。而这,就是温州糯米饭的密码,是温州清晨最动人的风景,是他旅程中又一段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