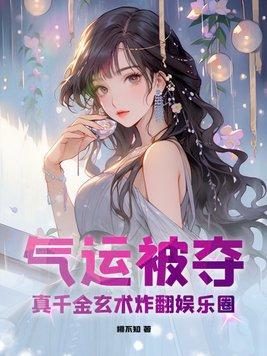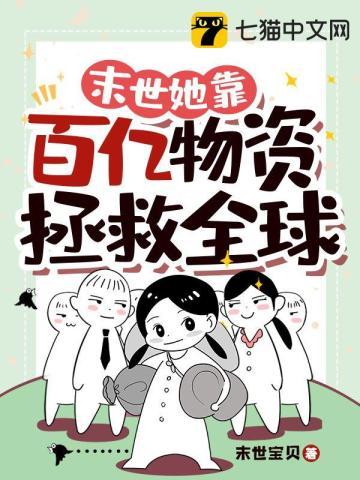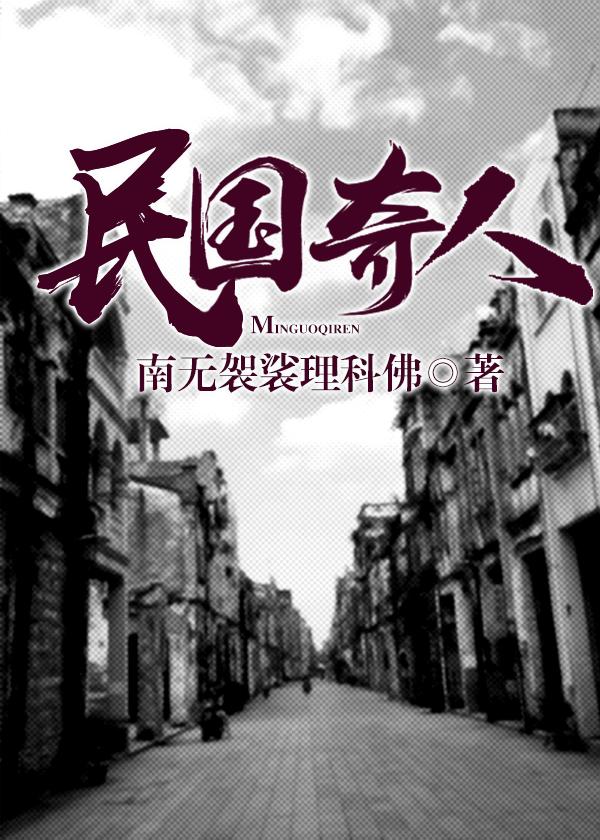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足迹在哪里查找 > 第51章 初到南京秦淮灯火映照鸭血粉丝(第1页)
第51章 初到南京秦淮灯火映照鸭血粉丝(第1页)
南京南站的玻璃幕墙外,午后的阳光正斜斜地铺下来,像一层融化的金箔,给灰色的建筑镀上了暖融融的边。玻璃反射着天空的淡蓝,偶尔有云朵飘过,影子在幕墙上轻轻滑过,像谁用手拂过镜面。陆帆背着帆布包走出出站口时,最先钻进鼻腔的不是想象中城市的汽车尾气,而是一阵淡淡的桂花香——是南京的早桂,开得悄无声息,却把香气揉进了微凉的风里,混着秦淮河畔特有的水汽。这香气比杭州的桂香少了几分甜腻,多了几分清冽,像刚从井里捞上来的水,沾着点石头的凉。
他站在广场上愣了几秒,目光被眼前的人群轻轻勾住。有背着双肩包的学生,耳机线从卫衣口袋里露出来,跟着脚步轻轻晃,嘴里哼着模糊的调子,应该是南京本地的民谣;有推着行李箱的旅人,箱子轮子在地面上“咕噜咕噜”响,停在路边低头看导航,屏幕亮着,上面是老门东的地图;还有穿着蓝色工装的电动车师傅,车筐里放着个透明的玻璃碗,碗里是深紫色的糖芋苗,泡在琥珀色的糖水里,碗沿还凝着点水珠,冒着若有若无的热气。师傅看到陆帆盯着碗看,笑着问:“小伙子,要去老门东不?十块钱,比地铁快,还能带你看沿途的老城墙。”
陆帆摆了摆手,笑着道谢。他发现南京的节奏似乎比杭州慢了半拍,连人们说话的语调,都带着点江淮方言特有的软糯,像浸了温水的棉花,裹着人的心。帆布包在肩上沉甸甸的,侧兜里的甜面酱罐轻轻撞着腿,罐口的保鲜膜还裹得严实,能隐约闻到里面黄豆和黄酒的混合香气——那是张叔的手艺,熬了两个小时的酱,连罐沿沾的一点都被张叔用袖口擦得干净。他抬手摸了摸包外侧的补丁,深蓝色的土布是李阿婆给的,上面还能看到细微的棉线纹路,那是阿婆缝茶袋时剩下的边角料,陆帆自己缝的补丁,针脚有点歪,却很结实,陪着他从松阳到杭州,再到南京,像个小小的护身符。
掏出手机时,屏幕还停留在粉丝“小桃”发来的消息界面,粉色的头像旁边,是小桃特意加粗的文字:“陆帆!南京的鸭血粉丝一定要去老门东附近的‘李记’!是本地人常去的老店,我上次去的时候,老板老李还送了我一小碟腌萝卜,超解腻!汤底是用老鸭熬的,鲜到掉眉毛,鸭肝处理得超干净,一点腥味都没有!”下面还附了张照片,是李记的招牌,木质的牌子上,“李记鸭血粉丝”五个黑色的字有点掉漆,却透着股让人安心的老味道。
跟着导航往地铁站走时,脚步在广场边的小吃摊前忍不住停了下来。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头发绾在脑后,用一根银色的发簪固定着,发簪的末端磨得发亮,是戴了几十年的老物件。她围着藏青色的围裙,围裙上印着“南京味道”西个红色的字,洗得有点发白,边角还缝了块米白色的补丁,是阿姨自己缝的,针脚细密。她的摊子不大,铁皮柜擦得锃亮,上面摆着两个冒着热气的大桶,桶身用红色的油漆写着字,一个是“梅花糕”,一个是“糖芋苗”,字体圆圆的,像小孩子写的。
阿姨正用小勺子给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装糖芋苗,勺子在碗里轻轻转了一圈,确保每个芋苗都裹上糖水,最后还不忘从旁边的小罐里抓出一小撮桂花,撒在碗面上,金色的桂花落在琥珀色的糖水里,像撒了把碎星星。“姑娘,慢走啊,”阿姨的声音软乎乎的,带着点南京话的尾音,“下次再来尝我的梅花糕,刚出锅的最香!”
陆帆凑过去时,正赶上阿姨给梅花糕模具加料。模具是黄铜做的,像一朵朵并排的小梅花,每个“花瓣”里都灌满了面糊,面糊是乳白色的,还冒着点小泡泡。阿姨用小勺子往每个“花瓣”里塞了点豆沙馅,豆沙是深红色的,看起来很细腻,“这豆沙是我自己熬的,”阿姨注意到他的目光,笑着解释,“用的是安徽的红豆,泡了一夜,熬的时候加了点冰糖,甜而不腻。”她又在每个“花瓣”里嵌了一颗小元宵,白色的元宵滚圆滚圆的,再撒上葡萄干和红枣碎,最后拿起铁板盖在模具上,“滋滋”的热气从模具缝里冒出来,带着面粉的清香和豆沙的甜,飘得很远。
“小伙子,要一个梅花糕不?”阿姨抬头看见他,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朵盛开的菊花,“刚出锅的,热乎着呢,甜口咸口都有,咸口的加了肉松,也好吃。”
“好,要一个甜口的。”陆帆掏出手机扫码时,阿姨己经用一根竹签从模具里挑出了一个梅花糕——金黄色的外皮边缘烤得有点焦脆,像撒了层碎金,上面淋了层透明的糖霜,还撒了把彩色的糖针,红的、绿的、黄的,像撒了把星星。他接过竹签,指尖刚碰到梅花糕的外皮就赶紧缩了回来,有点烫,只好用两根手指捏着竹签的末端。
咬一口,外皮是脆的,“咔嚓”一声,里面的面糊却软得像云朵,裹着豆沙馅的甜,刚好中和了外皮的焦香。小元宵煮得糯叽叽的,咬开后没有硬芯,混着葡萄干的微酸,一点都不觉得腻。“好吃吧?”阿姨一边给下一个客人装糖芋苗,一边跟他搭话,手里的动作没停,“我们南京的梅花糕,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面糊里要加酒酿,才有这股子清香味。你是外地来的吧?听口音不像本地的。”
“嗯,从杭州来的,专门来吃南京的美食。”陆帆咬着梅花糕,说话有点含糊,嘴角沾了点糖霜,他赶紧用手背擦了擦,“阿姨,您知道老门东的‘李记鸭血粉丝’吗?我想去那尝尝。”
“知道知道!”阿姨眼睛一亮,放下手里的勺子,手往东边指了指,“你坐地铁1号线到中华门站,出来走十分钟就到了。那家店开了二十年了,老板老李是个实在人,汤底是用老鸭熬的,每天天不亮就开始炖,要熬三个小时呢!”她顿了顿,又凑近了点,像是在说什么秘密,“你去了一定要点‘全家福’,鸭血、鸭肝、鸭肠、鸭肫都有,再配个锅巴,泡在汤里吃,锅巴吸了汤,香得很!别去夫子庙那些网红店,都是骗游客的,汤里加了味精,没老李那家正宗。”
陆帆谢过阿姨,手里举着梅花糕,慢慢往地铁站走。阳光穿过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己经开始泛黄,边缘卷了起来,像老人干枯的手掌,却依旧透着点绿。风一吹,叶子“沙沙”地响,偶尔有几片落下来,飘在路边的花坛里。花坛里种着月季,粉色的花瓣还带着露水,沾着点泥土,和桂花的香气混在一起,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
地铁1号线的站台很干净,蓝色的座椅沿着墙壁排开,坐着几个乘客。有个老奶奶正给怀里的小孙子喂糖芋苗,小孙子大概三岁,穿着红色的外套,手里抓着个玩具车,嘴里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老奶奶用小勺子舀了一点糖芋苗,放在嘴边吹了吹,确认不烫了才喂给孙子,孙子的嘴角沾了点糖水,老奶奶用一块印着小碎花的手帕轻轻擦着,动作慢得像在珍惜一段珍贵的时光。
陆帆找了个角落站着,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地铁从地下钻出来时,外面的景色一下子亮了起来——先是现代化的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亮得晃眼;然后是带着老南京味道的青砖灰瓦房子,屋顶上晒着被子,淡蓝色的被单在风里飘着;再往后,就能看到爬满藤蔓的老城墙,灰色的砖块垒得高高的,墙头上长满了低矮的杂草,还有几株爬山虎,绿色的藤蔓顺着墙面往下垂,像给城墙披了件绿披风。广播里的女声温柔地响起来:“各位乘客,中华门站到了,请从左侧车门下车,本站可前往明城墙遗址、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祝您旅途愉快。”
跟着人流走出地铁,刚上地面就被一股厚重的历史感裹住——不远处就是明城墙的遗址,灰色的砖块上还能看到模糊的刻字,是几十年前留下的,有的刻着名字,有的刻着日期。城墙下有几个老人在下棋,石桌上摆着一个搪瓷杯,里面泡着绿茶,茶叶浮在水面上,像一片片小叶子。老人下棋的动作很慢,每走一步都要琢磨半天,棋子落在棋盘上的“啪啪”声,和远处卖糖葫芦的吆喝声“糖葫芦——甜又甜——”混在一起,成了最鲜活的市井声。
按着阿姨指的方向走,路过一条窄窄的巷子,巷子口挂着个红色的木牌,上面写着“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字是用毛笔写的,墨色浓淡相宜,还带着点笔锋的力道。巷子里的路面是青石板铺的,被人踩了几十年,己经磨得发亮,缝隙里长着点青苔,下雨天会滑,现在倒是干爽,踩在上面能听到“哒哒”的声音。两边的房子都是青砖灰瓦的老建筑,门楣上挂着红灯笼,有的门口还摆着盆栽,是几株月季,粉色的花瓣衬着灰色的墙,像幅刚画好的水墨画。
巷子里的小吃摊一个挨着一个,热闹却不拥挤。有个卖糖画的老爷爷,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个铜勺,勺里装着融化的糖稀,金黄色的糖稀在阳光下亮晶晶的。老爷爷的手腕很稳,铜勺在青石板上“沙沙”地画着,不过几分钟,就画出了一只腾飞的龙,龙的鳞片、爪子都很细致,最后他用一根竹签粘在糖画上,递给旁边的小男孩,小男孩接过,高兴得蹦了起来。
往前走几步,是个卖盐水鸭的摊子,玻璃柜里摆着刚斩好的鸭块,鸭皮是白色的,带着点淡淡的黄色,肉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很嫩。摊主是个中年大叔,穿着白色的褂子,手上戴着一次性手套,正给客人切鸭腿,“我们家的盐水鸭,用的是南京本地的麻鸭,”大叔一边切一边介绍,“卤汁里加了八角、桂皮、香叶,还有点陈皮,卤了两个小时,吃起来不腻。你要是想带走,我给你真空包装,能放三天。”
再往前,是个卖活珠子的摊子,摊主是个大姐,竹篮里装着一个个白色的蛋壳,上面写着“活珠子”三个字。大姐掀开盖子,里面的汤汁冒着热气,香味飘得很远,“小伙子,要不要尝尝活珠子?”大姐热情地招呼,“要先喝汤再吃肉,汤最鲜,里面的蛋也好吃,煮得刚好好,不老。”陆帆摇了摇头,大姐也不介意,笑着说:“没事,下次再来尝,很多人第一次都不敢吃,吃了就爱上了。”
手里的梅花糕己经吃完了,竹签被他小心地放进了路边的垃圾桶。走到巷子深处,终于看到了“李记鸭血粉丝”的招牌——木质的牌子挂在门楣上,黑色的“李记鸭血粉丝”五个字有点掉漆,边缘用红色的漆描了一圈,是去年重新描的,还很鲜艳。店面不大,也就二十来平米,门口摆着两张红色的塑料桌,桌腿有点歪,用一块石头垫着。有个穿着校服的姑娘正坐在那吃粉丝,面前的碗里冒着热气,她一边吃一边跟对面的同学说笑,嘴角沾了点辣油,自己却没发现,同学笑着指了指她的嘴角,她赶紧用纸巾擦了擦,脸一下子红了。
陆帆掀开门帘走进去,店里的热气一下子裹住了他——不是空调的暖,是熬汤的蒸汽,混着鸭肉的鲜,扑面而来,带着点烟火气。天花板上挂着几盏黄色的灯泡,光线有点暗,却很暖,灯泡上还沾着点油烟的痕迹,是常年熬汤留下的。墙上贴满了老照片,用透明胶贴在墙上,防止掉下来。有一张是老板老李年轻时的照片,穿着白色的褂子,手里拿着长柄勺,站在灶台前,笑得很年轻;有一张是十几年前的老门东街景,青石板路上还没有这么多游客,只有几个推着自行车的居民,自行车上挂着菜篮子;还有很多食客的合影,有老人,有小孩,有情侣,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照片的边缘己经泛黄,却透着股温暖。
“小伙子,吃点啥?”柜台后的老板抬起头,声音有点哑,是常年在灶台前熏的。他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里掺着点白,戴着顶白色的厨师帽,帽檐下的眼睛很亮,正盯着陆帆手里的帆布包看——大概是觉得这包有点眼熟,像老物件。柜台后的灶台上,摆着一个巨大的不锈钢汤锅,锅盖掀开着,乳白色的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里面能看到整只的老鸭,鸭皮是淡黄色的,浮在汤面上,旁边还飘着几片生姜和葱段,姜是老生姜,皮有点皱,葱段是本地的大葱,绿色的叶子己经蔫了,却依旧带着香气。
“老板,要一份全家福鸭血粉丝,再加一份锅巴。”陆帆走到柜台前,指了指汤锅,“听说是用老鸭熬的汤?”
“可不是嘛!”老李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朵菊花,“每天凌晨三点就开始炖,用的是南京本地的麻鸭,肉质嫩,熬出来的汤才鲜。你看这汤,”他用长柄勺舀了一勺,汤在勺里泛着乳白色的光,能看到里面细微的油花,“没有加任何添加剂,就是老鸭、生姜、葱、料酒,熬三个小时,熬到鸭子脱骨,汤才够浓。”他一边说,一边从旁边的不锈钢盆里捞起鸭血——是新鲜的鸭血,切成了一厘米见方的小块,暗红色的,表面很光滑,像块小小的红宝石,“这鸭血也是每天早上从屠宰场拿的,新鲜得很,煮的时候不能煮太久,不然就老了,咬起来像橡皮,我一般就煮两分钟,刚。”
陆帆看着老李熟练地操作,每一个动作都透着几十年的经验。他先在一个白色的粗瓷碗里放上粉丝,粉丝是细白的,是用绿豆做的,老李抓了一把,不多不少,刚好铺满碗底,然后把粉丝放在漏勺里,伸进旁边的沸水里烫了十几秒,粉丝立刻变得透明,软乎乎的。接着,他依次往碗里加配料——先放鸭血块,码得整整齐齐,像小块的红宝石;然后是切得薄薄的鸭肝,淡褐色的,切得很均匀,大概两毫米厚;再是撕成条的鸭肠,淡粉色的,洗得很干净,没有一点杂质;最后是切成片的鸭肫,淡红色的,还切了花刀,煮出来会卷起来,好看又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