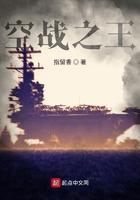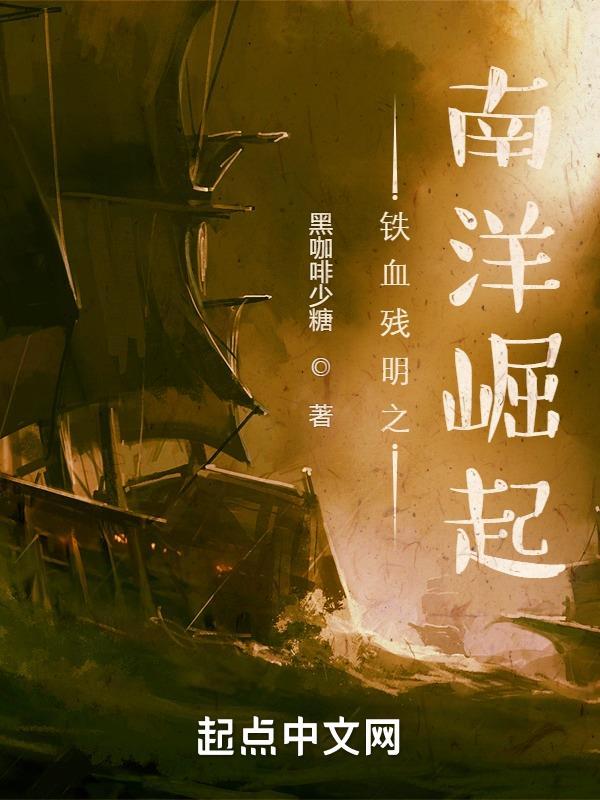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大清王朝兴起的过程 > 第1章 孤城血玺(第1页)
第1章 孤城血玺(第1页)
大明辽东,宁远孤城。袁崇焕手握尚方宝剑,却无兵无粮。朝中阉党横行,后方将领离心,城外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八旗铁骑滚滚而来。绝境之下,他竟收到一箱来自京城的“厚礼”——打开竟是魏忠贤送来催命的血诏与空印……袁崇焕沉默半晌,忽然下令:“取火油,烧城。”
---
天命十一年,正月,辽西走廊。
风像是从地狱深处刮出来的,卷着冰碴子和雪沫,抽打在宁远城灰黑色的城墙上,发出凄厉如鬼嚎的呼啸。旌旗被冻得硬邦邦的,勉强在城头猎猎作响,那声音不似鼓舞士气,倒像是绝望的呜咽。极目所至,旷野衰草枯折,白茫茫一片,唯有远处地平线上,一道蠕动的黑线在不断变粗、逼近。
那是十三万后金八旗铁骑掀起的雪尘,马蹄声闷雷般滚过冻土,即便隔着十数里,那股子踏碎山河的凶戾之气,己压得人心口发慌,喘不上气。
宁远,这座关外孤悬的堡垒,此刻真如怒海狂涛中即将倾覆的一叶扁舟。
袁崇焕独立在北墙敌楼前,身披一件半旧青袍,外罩冷锻铁甲,甲叶边缘己见了锈痕。寒风撕扯着他颌下清髯,面容冻得青白,唯有一双深陷的眼,沉静得骇人,死死盯着远方那铺天盖地的敌军。那目光,似要穿透漫天风雪,将敌酋努尔哈赤的虚实看个分明。
他身后的宁远城,与其说是一座军事重镇,不如说是一座巨大的难民营、伤兵营与堡垒的畸形结合。自广宁溃败,溃兵、逃难的百姓潮水般涌入这最后的屏障,挤满了每一条巷道,每一处角落。缺胳膊少腿的伤兵倚在背风的墙根下,眼神空洞地望着灰霾的天空,呻吟声被风声盖过,只余下扭曲痛苦的面容。妇孺蜷缩在临时搭起的窝棚里,冻得瑟瑟发抖,偶尔有压抑的啜泣传出,旋即又被风声掐断。
城头上,守军兵士们口鼻呼出的白气顷刻凝成霜花,挂在眉睫鬓角。他们紧握着手中为数不多的火铳、长矛,或倚着斑驳的垛口,或机械地搬运着滚木礌石。人数太少了,稀稀拉拉,面对城外那无边无际的敌军,这点守备力量薄得像张纸。许多人的棉衣破旧,难以御寒,冻得通红的脸上却透着一种近乎麻木的坚毅——退无可退,身后即是家园,虽远在关内,但退了,就什么都没了。
“粮草还能支撑几日?”袁崇焕开口,声音沙哑,像是生锈的铁片在摩擦。
身旁的参将周文郁脸色比天色还难看,低声道:“回大人,省着吃,最多……最多五日。箭矢不足三万,火药用一点少一点,红夷大炮的实心弹仅余七十余发,霰弹也快见底了。伤兵营里,金疮药早己用完,连干净的布条都寻不出了……”
袁崇焕沉默,指节在冰冷的垛口上无意识地叩击着。五日。十三万虎狼之师,连一天都嫌太长。
这些,他何尝不知。自请缨出关的那一天起,粮饷、兵员、器械,哪一样不是求爷爷告奶奶,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朝堂之上,那个九千岁魏公公把持朝政,只顾着给他那生祠贴金箔,辽东将士的死活,几时真正放在心上过?陛下深居宫中,这些急报,又能看到几分?
他腰间那柄尚方宝剑,此刻沉甸甸的,冰凉的剑鞘贴着肌肤,却给不了一丝暖意,反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剑,可斩临阵脱逃者,可斩不从号令者,却斩不断阉党的黑手,斩不来救命的粮草,更斩不退城外的十三万铁骑。
“满桂和祖大寿那边……还是不肯分兵来援?”袁崇焕又问,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周文郁的头垂得更低:“满总兵说……说他山海关防务更重,无旨意不敢妄动。祖将军……他……”周文郁咽了口唾沫,艰难道,“他说所部兵少,恐遭鞑子围点打援,请……请经略大人体谅。”
袁崇焕嘴角极轻微地抽搐了一下。体谅?何尝不知这些辽西旧将的心思。他们或是阉党门下,或拥兵自重,对自己这个空降的“袁蛮子”本就心存轻视,如今宁远被围成铁桶一般,谁肯来陪葬?离心离德,早己不是一日之寒。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踏着冰碴传来。一名亲兵顶着风雪奔上城楼,单膝跪地,声音带着喘:“报——经略大人!京城……京城来人了!说是九千岁有厚礼送至!”
袁崇焕霍然转身,周文郁及周围亲将的目光瞬间都聚焦过来。京城?厚礼?在这个关头?
风雪似乎都小了些,所有人心头都升起一丝荒诞的、不敢期待的希冀——难道是朝廷终于想起了宁远?是援军?是粮饷?
“人在哪?”袁崇焕的声音依旧平稳。
“在……在经略府门外。”
“带过来。”
来的是一名太监,面白无须,裹着厚厚的锦裘,却被冻得鼻涕首流,眼神里透着股京城来的倨傲与对边塞苦寒的嫌恶。他身后跟着几个小太监,抬着一口沉甸甸的描金紫檀木箱。
“袁大人,接旨意吧。”那太监尖着嗓子,也懒得寒暄,更不行礼,仿佛只是来丢一件垃圾。
没有圣旨,只有“旨意”。袁崇焕心下一沉,周围将领刚亮起些微的目光又迅速黯淡下去。
袁崇焕微微躬身:“臣,恭聆九千岁训示。”
太监清了清嗓子,拿腔拿调:“九千岁体恤尔等边关辛苦,特赐下厚礼,助袁大人破敌守城。望袁大人休负皇恩,休负九千岁期望,早日克竟全功!”说罢,示意将木箱抬上前。
那箱子做工精美,却与这残破的宁远城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