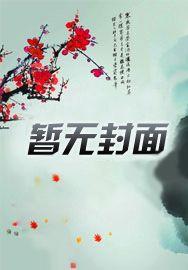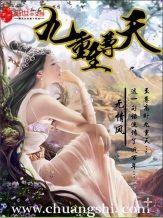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尘泥中的王旗怎么画 > 第5章 铁芒初绽(第1页)
第5章 铁芒初绽(第1页)
“橐龠”的轰鸣声日夜不息,成为了北壑村新的背景音。那沉重而规律的喘息,不再是怪异的杂音,而是力量与希望的象征,深深烙进每个村民的心里。炉火在水力鼓风的持续吹拂下,终于稳定地维持在了足以熔化矿石的高温。
经过数次失败的调整——调整投料比例、改进炉膛结构、摸索鼓风强度与火焰温度的关系——冶炼过程逐渐变得可控。
这天黄昏,当王康用长铁钳(用之前那块“砺锋铁”勉强打制)从白炽的炉膛里夹出坩埚,将炽热的、粘稠的、闪烁着刺目光芒的金属液浇入预先准备好的粗糙石范(模具)时,所有围拢在周围的工匠和村民都屏住了呼吸。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硫磺味和金属腥气,热浪灼人,但没人后退一步。他们的眼睛死死盯着那缓缓注入凹槽的、如同地心岩浆般的亮红色流体。
这一次,没有迅速冷凝成多孔蜂窝状的渣块。液体在石范中缓缓流动,填充,表面反射着落日余晖,呈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美。
等待冷却的过程无比煎熬。王康亲自守着,不时用树枝小心翼翼地拨开表面的浮渣。夜色渐深,有人点起了火把,橘色的光芒跳动着,映照着一张张紧张而期盼的脸。
终于,当那金属块彻底失去红光,变得暗沉时,王康用钳子将其夹出,放在一块厚木板上。它不再是一块畸形的疙瘩,而是一块略显粗糙但形状规整的、巴掌大小的长方块。表面还带着铸造留下的纹理和些许气孔,但整体质地肉眼可见地均匀了许多。
王康捡起地上另一块石头,深吸一口气,用力砸向那暗沉的金属块。
“铛!”
一声清脆响亮、带着明显金属颤音的交击声迸发出来,迥异于之前砸在矿石或废渣上的闷响!
暗灰色的表面被砸击处,露出了一小片银白色的、致密的金属光泽。
人群中发出一片压抑不住的惊呼。
王康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他拿起那块“铁锭”,入手沉甸甸的,冰凉而坚硬。他用“砺锋铁”的尖端用力去划,只留下一道浅白的划痕,而“砺锋铁”的尖端却微微卷钝了。
硬度、韧性,都远超之前的所有产物。
虽然远谈不上精良,含碳量可能不均,杂质依然不少,但这确确实实是真正意义上的、可用于锻打的生铁!
“成了……真的成了……”石叔声音颤抖,伸出粗糙的手,想要触摸,又怕玷污了这神迹般的造物,最终只是虚悬在上面,老泪纵横。他打过石头,磨过骨器,何曾想过能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甚至参与“炼”出这样一块铁?
黑娃激动地一拳砸在旁边的大树上,树叶簌簌落下:“好!太好了!有了这铁,看谁还敢来欺侮咱们!”
人群沸腾了。连日来的疲惫、怀疑、恐惧,在这一刻被巨大的喜悦和自豪冲散。他们看着那块不起眼的铁块,仿佛看到了更锋利的锄头、更坚固的矛头、更安全的屋舍……看到了活下去的真正底气。
李嫂也挤在人群里,脸上的表情复杂无比,最终化为了深深的敬畏,悄悄往后缩了缩,不敢再发一言。
王康握着那块尚有余温的铁锭,感受着那份沉甸甸的实质,心中亦是波澜起伏。这是零的突破,是知识转化为力量的明证。它证明了他的道路是可行的。
但他很快冷静下来。一块铁锭远远不够。产量、质量、稳定性都需要极大提升。燃料危机依旧存在,水力鼓风机需要维护和改进,合格的工匠更是凤毛麟角。
“黑娃,带人看好炉子,鼓风不能停,按刚才的法子,继续炼!”
“石叔,挑两个手最稳、最细心的人,跟我学打铁!”
喜悦必须转化为持续的生产力。他立刻着手,利用这第一块成功的铁锭,优先打造几样最关键的工具:一把更结实耐用的铁锤,几根不同规格的铁錾(chisel),以及……一把真正意义上的铁斧。
有了更好的工具,才能制造更好的工具,正循环才能开始。
接下来的几天,村里唯一能听到的、压过“橐龠”声的,就是那从王康临时搭建的锻棚里传出的、富有节奏的“叮当”打铁声。火星在昏暗的棚子里西溅,王康带着两个挑选出来的青年,轮动着重了许多的新铁锤,反复锻打着烧红的铁料,将其延展、塑形。
第一把铁斧诞生时,黑娃迫不及待地抢过去,对着一段之前需要砍上好半天的硬木挥去。
咔嚓!
一声干脆利落的脆响,木桩应声而断,断面光滑!
效率的提升是肉眼可见的。砍伐木材的速度加快了,处理材料也更得心应手。虽然铁器依旧宝贵,无法人手一把,但核心工作的效率得到了质的提升。
北壑村,这个位于乱世边缘、仿佛被遗忘的角落,正以一种笨拙却坚定的方式,孕育着超越这个时代贫瘠土壤的锋芒。
这块小小的、粗糙的铁芒,终于刺破了绝望的茧壳。
然而,王康深知,铁器带来的不仅是力量,还有更大的风险。锻造的声响、日夜不息的炉火、以及……最终无法完全隐藏的、属于铁器的独特寒光,都像黑暗中的灯塔,可能会吸引来远超张二爷家丁的恶狼。
就在村民们还沉浸在初步成功的喜悦中时,负责东面瞭望哨的阿木,连滚带爬地冲回了村子,脸色煞白,上气不接下气:
“康哥!东面……官道上来了好多骑马的!打着旗号……往,往张家庄的方向去了!”
新的变数,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