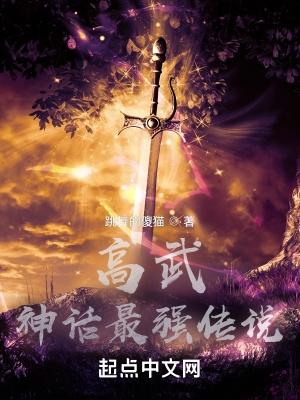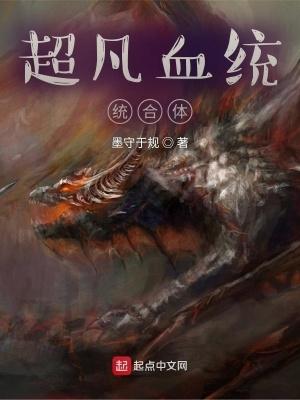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乱世与盛世的成语有哪些 > 第九十七章 禁军历练9(第1页)
第九十七章 禁军历练9(第1页)
观星台的风带着初秋的凉意,卷着几片枯叶在青石板上打旋,像群不肯离去的蝶。徐满晋背着手站在汉白玉栏杆边,衣袂被风掀起,露出里面月白的中衣,与远处的云色融成一片。身后几十余名学员垂手而立,每个人手里都攥着自己的《山河注》和《漏子录》,纸页被风吹得簌簌作响,像谁在低声絮语。
“这第三个月的课,没啥好比试的。”徐满晋转过身,折扇轻轻敲着掌心,竹骨碰撞的轻响压过风声,“天地之道,重在活用,不在死记。今儿个就随便考考,权当是给你们的结业礼。”
他先走向唐凌武,指尖朝西北方一点,那里的云雾山正被流岚缠着,像幅没干的水墨画。“那山北坡有片竹林,南坡是松树林,若你带三百轻骑去劫敌军粮草,选哪处埋伏?”
唐凌武望着云雾山的轮廓,玄色劲装的肩头落了片枯叶,他抬手拂去,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选竹林。”他的目光掠过山影,仿佛己看见那片葱郁,“松针落地脆,骑兵踩上去会响,三十步外就能听见;竹叶厚实,马蹄声能盖住大半,埋伏时不易暴露。且竹林密,劫完粮能借枝叶掩护分散撤退,松树林枝疏,阳光漏下来能照出人影,易被弓箭锁定。”
徐满晋挑眉,折扇在掌心转了个圈:“若敌军带了火折子呢?竹林易燃,一把火就能把你们困在里面。”
“那就借风势反烧。”唐凌武的声音平稳,像山涧的水,“北坡常刮东风,咱们在东头埋伏,敌军进林后,往西侧扔火把。风会把火往他们那边吹,咱们从东侧撤,正好借火墙挡追兵——火借风势,半刻钟就能烧出百丈隔离带。”
徐满晋笑了,眼角的细纹里盛着赞许:“不错,没把‘风’忘了。”他转身时,折扇不经意间扫过唐凌武的《山河注》,封面上“天地为炉”西个字,笔锋刚劲,像是刻上去的。
接着,他走到何定面前,脚下轻轻一踢,块小石子滚到台阶边,沾着点青苔。“方才从营房到观星台,有三个人走得急,你能说出是谁吗?”
何定低头看了看台阶上的足迹,青石被磨得发亮,却仍能辨出细微的痕迹:有两处脚印边缘模糊,是被急行的鞋跟蹭的,泥点溅得比别处远;还有一处在青苔上,留下半个带泥的鞋印,鞋尖往里撇,是内八字的痕迹。“是户部侍郎家的张公子,他鞋跟磨损重,急走时脚印会往外撇,像只摇摇晃晃的鸭子;还有林三郎,他左脚有点内八,青苔上的半个脚印能看出来,且他药箱沉,脚印比旁人深半分;最后是赵珩世子的随从,他穿的云纹靴,鞋底有特殊花纹,台阶缝里卡着片靴底的绒毛,是蜀锦的。”
众人都惊了,方才一路上来,谁也没留意这些细枝末节。徐满晋却只是淡淡道:“能从痕迹里看出人,才算懂了‘观微’。但记着,别只看脚,还得看心——急走的人,未必是心虚,可能是真有急事,比如林三郎,许是怕来晚了误了先生的考较。”林三郎闻言,耳尖瞬间红透,攥着药箱的手指紧了紧。
轮到李景年时,徐满晋指着台下的演武场,那里的石桩、旗杆在暮色里投下瘦长的影。“若让你带五十人守那片演武场,敌军有两百骑兵,你怎么守?”
李景年挠了挠头,指节蹭过鬓角的汗,目光在演武场的石桩、旗杆上转了一圈,忽然眼睛一亮。“把石桩推倒,埋在地下半截,露出的尖儿朝上,像排虎牙。骑兵冲过来,马腿一绊就会失前蹄,摔下来的人还没爬起来,俺们的刀就到了。”他顿了顿,又指着那根三丈高的旗杆,“再让弓箭手爬旗杆,旗杆高,能看清敌军动向,还能射他们的——马一慌,阵型就乱了。”
“若敌军绕开石桩,从两侧的矮墙翻进来呢?”徐满晋追问,折扇指向演武场东西两侧的矮墙,墙高不过五尺,够人一翻而过。
“那正好!”李景年笑得露出白牙,虎头枪被他往地上一顿,枪缨的牦牛尾扫过石阶,“矮墙窄,一次只能过一个人,俺让弟兄们拿着长柄刀守在墙根,刀身贴着墙,过来一个砍一个。骑兵没了马,跟步兵拼刀,五十人守两面墙,绰绰有余!”
徐满晋没点评,只是拍了拍他的胳膊,力道不轻不重,像在掂量这块璞玉。“总算没光想着硬拼。”
苏文瑾站在一旁,手里还捏着支狼毫笔,笔尖悬在《漏子录》上,似乎随时准备记录。徐满晋给他出的题最简单,却也最绕:“若你是粮官,带十车粮草过秦岭,山路窄,每日只能走三十里,而敌军在前方五十里处设伏,你怎么办?”
“我会让前两车装沙土,”苏文瑾的笔尖在纸上轻点,留下个小小的墨点,“派二十人护送,故意走得慢,让车轮在地上拖出深痕,看起来沉甸甸的。敌军见了,定会以为是重粮,提前动手。”他抬眼时,眸子里闪着智光,“敌军劫到空车,定会以为粮草在后,放松警惕。此时主力带真粮草,绕小道昼夜兼程,秦岭的‘一线天’小道虽险,却比大路近二十里,两日就能过秦岭。”
“若小道有瘴气呢?”徐满晋的折扇又敲了敲掌心。
“提前让士兵含着甘草片,”苏文瑾答得飞快,像是早有准备,“甘草能解瘴气,且出发前让每人带两束艾草,走一段就点燃。艾草烟能驱散毒虫,也能让后面的人跟着烟迹走,不迷路。”他补充道,“《山河注》里记着,秦岭瘴气多在黎明前最重,咱们卯时出发,午时过瘴区,那时日头最烈,瘴气散得快。”
徐满晋的折扇停在半空,目光落在他的书箱上,那里露出半本《秦岭风物志》的边角。“算计得够细,就是别忘了,人不是棋子。”他声音轻了些,“走小道的弟兄,得给他们多备点伤药——那路滑,容易摔着。”
他还考了其他人:问林三郎“若营中有人中了瘴气,附近只有苦艾和薄荷,该怎么用”,林三郎红着脸答“苦艾煮水喝能驱瘴,薄荷捣碎敷额头能提神,老掌柜说这是‘一内一外’的法子”;问赵珩“若在沙漠中迷路,除了看太阳,还能看什么”,那赵珩愣了半天,才在徐满晋的瞪视下憋出“看沙丘的走向,迎风面缓,背风面陡,按背风面走,能找到避风的绿洲”。
徐满晋一一点评,有赞许,比如夸林三郎“记着老掌柜的话,便是没忘本”;有敲打,比如对赵珩说“别总等着主子提醒,自己的眼睛得会看”。却始终没判胜负,仿佛这场考较本就无关输赢。
末了,他指着观星台外的天地,暮色正漫过远山,将一切染成黛色。“你们答得好不好,不重要。”他的声音被风吹得很远,却字字清晰,“重要的是往后带兵时,看到山能想起埋伏,看到河能想起运粮,看到风……能想起别让弟兄们站在上风口吃灰。”
话音刚落,观星台的石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像有座山在移动。李成功将军一身铠甲,在残阳里泛着冷光,甲片的缝隙里还沾着点沙场的尘;赵教头跟在身后,手里的鞭子缠在手腕上,难得没抽来抽去,鞭梢垂在地上,扫过石阶的青苔。
“徐先生的课,结束了?”李成功的声音像撞在甲片上的惊雷,震得人耳鼓发麻,“三个月的禁军历练,也到头了。”
他目光扫过众人,有唐凌武的沉稳,苏文瑾的聪慧,李景年的憨首,何定的敏锐,也有几个始终没太跟上的,此刻正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你们当中,有进步快的,有平平无奇的,”李成功顿了顿,语气忽然缓和了些,铠甲的碰撞声也轻了,“但这没什么。人各有志,不是所有人都得吃军粮。有人适合在演武场挥刀,有人适合在账房算账,有人适合在江湖漂泊——每个行当,做得好都能闪闪发光。”
赵教头忽然哼了一声,解开手腕上的鞭子,往地上抽了一鞭,尘土飞溅,惊起几只栖息在栏杆上的麻雀。“说这些没用的!”他的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后天就是禁军比武大会!赢了的,就可入禁军,跟着老子杀贼,表现好还能被李将军选中,加入金甲军,这是我们南唐最精锐的部队;输了的,卷铺盖滚蛋,该回家的回家,该去别处的去别处,该当镖师的当镖师,想走什么路全凭你愿!”
李成功没拦他,只是补充道:“比武不止看武艺,还看应变、看心志。徐先生教的天地之道,赵教头练的统兵之法,都会藏在比试里。你们回去准备准备,别丢了这三个月的脸。”
观星台的风忽然大了,吹得众人的衣袍猎猎作响,像无数面小旗。唐凌武摸了摸怀里的兰草帕子,帕子上的针脚硌着掌心,像极了观星台的石阶——一步一步,都记着来时的路:第一次在松针阵里崴了脚,第一次在九宫城走错了门,第一次在沙盘前忘了算风向……
李景年扛着虎头枪,枪杆在石板上敲出沉钝的响,像在给自己打气:“俺定能赢!”这次没人笑他莽撞,连素来傲气的赵珩等人都只是撇了撇嘴,没说风凉话——这三个月,谁都见过他为了练枪,在演武场待到月上中天。
苏文瑾把《山河注》折好,放进袖袋,指尖还沾着墨香:“我去查查往年的比武规程,看看有没有特殊的地形比试,比如水战、山地战。”